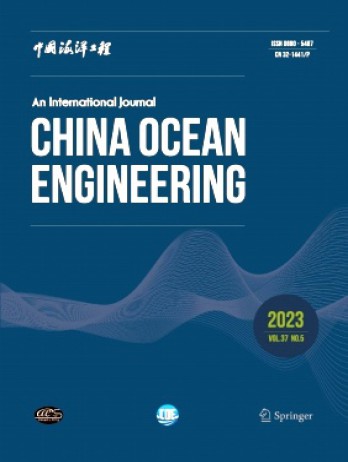欧美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欧美文学论文篇(1)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欧美文学论文篇(2)
一 冷战时期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东西方对峙的中心。美国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而后者由于经济困难及国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因此西欧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就使共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为双方结盟奠定了基础。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了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1liance),战后美欧关系的总体特征由此确立。
冷战的爆发和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构成了当代美欧关系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美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冷战新格局下大西洋两岸的互动,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西洋联盟展开了持续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发表的有关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专著就有近百部,专题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从研究方法来看,有的采用微观方法,侧重对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有的采用中观方法,着重考察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欧关系;有的采用宏观方法,对战后较长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一些研究侧重从理想主义的视角解释美欧关系,认为美欧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故大西洋联盟坚不可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的《铸造联盟的成功:美国和西欧》、比阿特丽斯・休赛尔(Beatrice Heuser)的《大西洋关系:分享理想与成本》、杰弗里・威廉姆斯(Geoffrey Williams)的《永久的联盟:欧美伙伴关系,1945~1984年》、托马斯・里斯卡盆(Thomas Risse-Kappen)的《民主国家间的合作:欧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坚持到底:欧洲联合和大西洋团结》。还有学者强调美欧关系的共同体属性,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1950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在他看来,美欧价值观的相互补充和对相互需要的高度反应能力,比共同安全威胁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团结。
与理想主义的诠释相比,更多的研究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西洋联盟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由于美欧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这一看法揭示了美欧关系矛盾复杂的一面,其症结在于双方在大西洋联盟内地位不平等,即美国充当盟主而西欧国家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角色,这种不平等是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而欧洲一体化也带有美欧冲突的基因,因为欧盟谋求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相抵触。虽然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它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被纳入大西洋合作的框架,即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美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它就会显现。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形势趋缓和西欧实力的增长,美欧关系初现调整,大西洋联盟内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此后双方关系虽在个别时期有所改善,但联盟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战后美欧关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冲突,即使在北约成立后美欧合作被认为是最密切的时期,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持续不断。
总之,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欧美学术界对美欧矛盾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性学者及其著述包括理查德・贝茨(RichardBetts)的《北约的中期危机》、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的《大西洋联盟的长期危机》、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大西洋危机》、沃尔特・哈恩(Walter Hahn)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合编的《大西洋共同体陷入危机: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关系》、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纷争的延续:大西洋共同体的危机和反应》、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的《欧美关系:持续的危机》、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的《大西洋危机:美国外交面对复兴的欧洲》、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的《脱离美国的欧洲?大西洋关系的危机》、伊莉莎白・舍伍德(Eliz-abeth Sherwood)的《陷入危机的盟友》、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西欧和美国:不确定的联盟》,以及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的《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界的研究,欧美的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有关于美欧关系特别是北约的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65年出版的《麻烦的伴关系: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一书,此外,还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到了拯救北约的时候了》、让・弗朗索瓦庞塞特(Jean Francois-Poncet)的《欧洲和美国:危机的教训》、罗伯特・谢策尔(RobertSchaetzel)的《精神失常的联盟: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以及保罗一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等著述。这些著述虽试图在美欧合作与冲突之间保持平衡,但对冲突的论述偏多,这从书名和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概言之,战后美欧关系既有合作的动力和基础,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这就决定了合作与冲突是当代美欧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冷战期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与此大体相一致,普遍认为美欧关系是一部纷争与合作的历史,基辛格用“麻烦的伙伴关系”来定义大西洋联盟当属恰当。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具有两个阶段性特点:其一,虽然合作是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方面,而欧美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但他们却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美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进入1960年代后,这种倾向尤其明
显,侧重论述美欧矛盾与冲突的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论述美欧合作的论著;强调美欧分歧的论者多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美欧合作与冲突的论述则相对平衡一些。其二,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北约体制下的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双边关系,而这也主要集中于安全关系。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相对不受重视,相关研究数量少且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实际相符,它折射了冷战格局对双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安全问题和安全关系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 冷战后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冷战的结束是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威胁的消失降低了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导致美欧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欧盟抓住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并要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调整又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双方不同战略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要想在这方面达成妥协与平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的混乱和大量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要求美欧不能立刻分道扬镳。因此,在调整中有合作、在合作中调整,就成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欧美学者的研究大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在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美欧在有关北约前途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矛盾,研究内容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分歧。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冷战后的世界逐渐尘埃落定、克林顿政府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取灵活态度从而使美欧关系趋于改善时,研究内容又转向强调美欧一致性。但“好”景不长,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导致美欧关系再起波澜。研究的侧重点也随之逆转,退回到对美欧分歧的强调。九一一事件之初,分析人士一度对美欧关系的改善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双方的分歧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分歧不仅涉及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更突出地反映在国际事务层面,包括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以及伊拉克战争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分歧。
总的看,冷战后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矛盾的,论证美欧分歧增多的著述与强调美欧一致性的著述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观点明显呈两极化。欧美学术界和思想库都存在所谓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乐观派认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的紧张不会对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联盟是建立在双方价值观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当前的摩擦同历史上的所有分歧一样,都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双方互示善意而及时得到解决。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表达的看法接近于这种观点。斯滕・赖宁(Sten Rynning)更是对大西洋联盟满怀信心,称北约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前途。悲观派则另执一词,称美欧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紧张的,而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曾经使双方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已不复存在,北约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大西洋联盟变得越来越敌对,北约进入了严重衰落的阶段。在悲观论者看来,欧盟加紧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表明了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和决心,这也将加速大西洋联盟的瓦解。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权力与虚弱》一文中直言:“当涉及到确定国家议程、界定威胁和挑战及制定和实施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就分道扬镳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悲观派对冷战后美欧关系趋于恶化的基本判断。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悲观论者的分析有着多元的角度。有的研究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人手,强调苏联解体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强烈冲击,认为一个制衡美国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不仅降低了美欧在安全问题上保持团结的需要,也鼓励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时间和精力以谋求联盟的共识和一致。也有的研究立足于国家和集团层面的分析,强调美欧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差异,认为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益,而欧盟则致力于实现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目标。还有的研究侧重于行为方式的分析,强调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的差异,欧洲人讲究谈判艺术,致力于取得共识和妥协,而美国则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异己。卡根对美欧这一差异的解释是欧洲来自水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洲人依赖外交是因为欧洲军事上弱小,美国人偏爱军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享有无与匹敌的军事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是因为这样见效快,又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也有分析将美欧的这一差异归因于双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双方在20世纪的不同经历和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欧洲人看来,战争对于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今后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而对美国人来说,除了越南战争,美国在其他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分析,即把美欧关系的变化与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个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同个性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变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总之,伴随着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而复杂的调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争论的情况看,乐观派和悲观论者大体上势均力敌,但后者略占上风,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明显一些。这种两极对立观点的交锋与冷战时期偏重于强调美欧分歧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的欧美研究者想当然地以为大西洋联盟是不容质疑的客观存在,因而能够以相对超然和从容的心态面对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但时过境迁,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欧美研究者在关注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时候,一些人的研究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美欧关系多了一些忧患和同情。
除了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论争,冷战后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欧盟及其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其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它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欧盟不仅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而被美国视为一个政治对话者。面对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崛起,美国较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双边关系。相应地,美国与欧盟关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冷战后发表的大部分相关著述虽仍旧一般性地指向美欧关系或大西洋关系,而未将美国与欧盟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论述触及到了欧盟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以美国-欧盟关系为主题的论著,例如凯文・费瑟斯顿(Kevin Feather-stone)和罗伊・金斯伯格(Roy H.Ginsberg)合著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变中的伙
伴》。此书运用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即复合相互依存范式,试图衡量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强度;埃里克・菲利帕特(Eric Philippart)和帕斯科莱恩・怀南德(Pascaline Winand)合编的《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一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则讨论了美国-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强调了欧盟在美国一欧盟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约翰・彼德森(John Peterson)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前景》主要讨论的也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中“欧洲”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的组织机构属性进一步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另有少数国家则不同时属于这两个机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组织机构内的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相悖。应当说,这一因素对现实的美欧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也给美欧关系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 围绕未来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
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两分法,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纷争。
如上所述,悲观论者的基本判断是冷战后的美欧(盟)关系在走向恶化。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深刻地改变了大西洋联盟。他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建立在欧美拥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的杂乱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及东西方在第三世界争夺的结束,曾经将欧洲人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不复存在,结果是美欧关系不可避免地陷于崩溃。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说,冷战结束后,欧美已不必再为促进民主和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推进市场经济及那些冷战期间体现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了。迈克・弗拉奥斯(Mike Vlahos)声称,冷战后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地区将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求获得更大的独立;欧洲人和日本人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走自己的路并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则坦言,世界上亲美国的态度有“显著的总体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持悲观论的理论学者认为,美欧关系今后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首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再亏欠美国,因为外部威胁的降低使欧洲待在美国保护伞之外的危险减小了。而对美国人来说,冷战后继续待在欧洲的动因似乎也在消退。戴维・卡莱欧(David P.Calleo)指出,随着孤立主义情绪抬头,美国人越来越质疑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高成本军事存在的理由,对继续花钱帮助已有能力为自身防务买单的欧洲人的理由也表示怀疑。关于北约的前途,有人认为它早已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从长远来看,北约注定要消失。这种看法的依据的是欧洲人希望北约消失,或者至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欧洲人控制的组织,法国特别想利用欧盟或者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一解释,“马约”(Maastricht Treaty)带有的“传染病菌”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瓦解,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概念明显反映了欧洲谋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意图。欧盟试图通过发展自主防务建立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霸权,从长远看,如果欧盟直接或者通过吸收西欧联盟而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解体,从而终结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保障。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的发表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都表明了欧洲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简言之,这些学者虽不否认美欧之间的某些关系是积极的,但强调双方关系中为数不多的积极面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欧美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了,而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矛盾在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增加,从而造成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与上述悲观判断不同,乐观派学者强调大西洋关系的深度。他们不否认美欧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但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冷战的结束并未使美欧(盟)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也乐观地看待北约的前途,认为它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加入北约即是证明。有人甚至称,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远没有变弱,冷战的结束反而加强了这种感情。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洲记忆犹新,欧洲人始终都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保持着警惕;而美国也从上世纪20年代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旧大陆,反而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些论者看来,美国与欧盟关系中有三个关键的成分:一是美国不反对甚至总体上支持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的努力,勒内・施沃克(Ren∈Schwok)认为,美国欢迎欧盟朝着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方向前进;二是美国同意在其不参加的情况下,允许欧盟使用北约的军事资产,包括运输和通讯系统等;最后,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指出的,美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除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立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也可以参与危机管理行动,并使用北约的资源。
不难看出,悲观论者对美欧关系的解释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间不可能有持久的联盟。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不承认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要么作为新的国家行事,抑或是如此虚弱以致于国际组织中仍将显现国家权力。受这种概念性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现实主义者对所谓的欧洲统一表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欧盟更接近于传统的国际组织,而非像德国、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因此欧盟不具有国际人格。现实主义范式不承认欧洲国家可以拥有和平的关系,更不接受欧盟与美国关系可以是非冲突的情形。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悲观论者强调大国之间的霸权竞争,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大国和集团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包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美欧重新焕发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双方都寻求在世界各地获得霸权地位。美国和欧盟的竞争主要在东欧展开,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也奉行同样的政策。这些论者经常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一个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就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
美欧之间的霸权竞争也反映在金融领域,悲观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观点,即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受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不仅如此,欧洲单一货币通过限制美国的政治选择,还将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有理由对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保持警惕,并应尽力加以阻止它的形成。马丁・费尔德斯坦(Mar tin Feldstein)指出,美国不支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就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
与悲观论者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向不同,乐观论者坚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多元趋势论,他们对解释性的、体系性的和预测性的理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采用“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是这一理论范式的倡导者。根据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关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众多不同的渠道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二是国际关系议程由众多的问题组成,不能将这些问题以任何清晰的或者模糊的等级固定下来;三是,当相互依存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政府将不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别的政府。费瑟斯顿和金斯伯格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大西洋两岸的众多渠道将美国和欧盟联系起来,而大量的问题组成了美欧关系的议程,这些问题不是以某种连贯和等级方式被固定下来;由于彼此间高度的复合相互依存,美国和欧盟都不再可能对对方使用武力。不过,复合相互依存论者对其他理论也并非全然排斥,有时甚至还采纳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国家通常是理性地行事,认为欧盟和美国根据形势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强调多元论之分析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认为国家并非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而且也并不总是理性地行事;对权力的追求并非国家唯一的外交政策目标。
从多元趋势论出发,乐观论者不接受霸权竞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欧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竞争。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欧达成了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分担协定,1995年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和《联合行动计划》(Joint Action Plan)是1958年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以来美欧关系中的一个实质性步骤。美国认为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伙伴,而是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几乎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同美国一起行动。文件中宣布的目标和大约120个具体行动,表明美欧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其程度比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任何国家集团的共识都要高,或许只有加拿大除外。他们还认为,欧美在处理欧洲安全危机方面仍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美国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加强了大西洋关系;由于欧盟尚不具备独立解决重大危机的能力,美国在西方联盟和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在金融问题方面,他们强调指出,虽然有一些美国投机者希望欧洲货币联盟出问题,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美国欢迎欧洲货币联盟。
除了在霸权竞争问题上的争论,两派学者还围绕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大做文章。悲观论者认为,冷战后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实行东扩来加强以西欧为核心的一体化。由于日益专注于内部问题,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少,也无意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趋向于建立保护主义的商业集团。欧盟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深化内部一体化、通过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联系,以及通过联系协议加强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则主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还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及中南美洲自由贸易的活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冲突,并使得冷战后的冲突日益经济化。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冷战结束后重商主义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将会发展,欧盟正日益变成一个堡垒,滥用反倾销措施,而美国也使用了过分的保护主义工具如“超级301”等。美国正在丧失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吉尔平预言多边主义将会被经济地区主义所取代,称“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sectoral)保护主义的混合体系正在取代多边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乐观派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欧盟并没有走向保护主义,因为建成后的单一市场比最初大部分专家预测的要开放和自由得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也更多地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减少国家控制的总趋势。他们同时指出,建立内部市场,以及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东欧、地中海国家签署联系协议,也不意味着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相反却表明了欧盟对外部是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同样,他们也不接受“贸易集团”的概念,不认为欧盟、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构成了某种“贸易集团”。在他们看来,这些安排都不是保护主义的,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歧视性安排,所有协议都是以自由贸易的原则为基础,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标准。美国不批评反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证明了欧盟的非歧视性质,而欧盟同样也没有反对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他们还指出,美欧合作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表明了双方都支持自由贸易,不想让贸易和农业冲突加剧双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紧张;这一成功确立了美欧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在世界上谋求合作领导地位的最佳证明。
四 结语
如文中所指出的,合作与冲突是贯穿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判断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到底孰轻孰重,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衡量的标准。如果以某种完美的和谐团结作为标准,那么,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非常突出;如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美欧合作又确实显得非常特别,不仅紧密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联盟时间也更加持久。伦德斯塔德认为,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证明战后美欧关系的密切程度:一是“欧洲人邀请美国到欧洲建立帝国”。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最担心美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而再次从欧洲撤退,为此它们主动采取了挽留措施,先是请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接着要求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障,并最终通过北约建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强大军事存在。二是美国“帝国”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后者大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美国则力促其控制下的最重要西欧地区实行一体化。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说,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是历史上一个大国首次一贯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将从前分裂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应当说,从历史的和比较分析的角度看,战后建立的大西洋联盟堪称世界史上迄今最持久、最成功的联盟。虽然联盟始终都存在内部冲突的因素,但在东西方冷战的基本格局之下,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定了美欧合作是主要的,而矛盾和分歧则受到抑制。同样,欧洲一体化在冷战格局下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它实际上被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中。所以,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确实是密切合作的“特殊关系”,尽管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欧美文学论文篇(3)
摘 要:近年加州学派对于前近代东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关于“欧洲中心论”的讨论是其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欧洲中心论”存在着两种颇为对立的理解:一种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另一种强调的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理解加州学派谈及“欧洲中心论”时的实际含义,对于合理评价其历史诠释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 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41-07
十余年来关于“加州学派”的讨论之中,“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话题之一。而且,无论是该学派的同情者,还是其批评者,对于“欧洲中心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痛加批判。然而,笔者发现,由于对“欧洲中心论”的界定不一、理解分歧,这些批评的指向实际并不一致,而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各自解释”,不但使得学术批评常出现“答非所问”之混乱感,而且“欧洲中心论”本身也成为一个大杂烩,如同随处可扣的帽子。细绎近年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对“欧洲中心论”的不同理解,它们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厘清这些观念上的区别,对于理顺学术批评中的相关问题、理解“加州学派”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混沌不明的“欧洲中心论”
如同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经常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命题,而如果说各种“主义”的定义难点在于见解纷纭,难以取得共识的话,“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于似乎很少有人尝试着对它进行定义。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尝试之中,林甘泉作过这样的表述:“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①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表述主要是受到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
显然,“欧洲中心论”并不代表一个学术实体,它包含的内容芜杂、牵涉面极广,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被冠以“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观点,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冲突。国内学术界较早接触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批判,当始于柯文的著作[注: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柯文对战后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进行了批评,其中帝国主义模式本身就站在前两种研究模式的对立面。在思想方法上,前二者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后者则反映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左派甚至激进派思潮,但都被装在“西方中心观”的篮子里。加州学派中抨击“欧洲中心论”最力的贡德·弗兰克,将以下学者列在“欧洲中心论”的代表名单中:斯密、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罗斯托、奇波拉、诺思、麦克尼尔、沃勒斯坦……,几乎囊括了所有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大家[注: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5页。]。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念彼此差别之大,可以不必赘谈。
沃勒斯坦,弗兰克的早期合作者和后来的主要论敌之一,曾经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作了一个归纳,简而言之,他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多种形态及其批评的多种形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在历史编纂学上,“用欧洲的独特历史成就来对欧洲支配近现代世界的原因”作出解释;2、社会科学的“普遍主义”倾向,“认为存在着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真理”,而其要害是“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3、文明的优越论和价值观,欧洲“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少是独特的)‘文明’世界”;4、“东方学”中体现出来的二元主义;5、对于“进步”观念及“进步”的“不可避免性”的强调,并将它“强加于人”[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马万利译,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概括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混乱而驳杂的,沃勒斯坦本人也指出这些“表现”“并不能必然地形成一幅连贯的图画”[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第71页。],而且,这五个方面的“表现”及“批评的多种形态”,事实上已经呈现出差别和矛盾。
欧美文学论文篇(4)
实际上美国的的确确如社会学家所称的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美国的软实力不单单是流行文化,文化大杂烩中有google、麦当劳、现代艺术博物馆、好莱坞、哈佛,众人耳熟能详。在欧洲甚至在文化感至上的法国,有2/3的电影打有英文字幕,而在图书译介上美国的统治地位更是如此。每1本德语著作译成英语,就有9本英语著作译为德文。而过去却是另一种情形。一百多年前,汉堡大学是世界大学的圣地,不少大学当时都对其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东京大学、霍普金斯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些现在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在仿照德国大学并巧妙结合了它的教学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忆往昔,欧洲大学光芒不再,开始探讨大学改革,而其参照对象乃后进之辈美国。
美国文化无处不在,但这对建立其真正的影响力似乎关系甚微。美国渗透到全球千千万万人的吃穿住行中,但他们并不认同每天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国。扬基帽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但并不是人人皆知它所代表的纽约橄榄队,更遑论热爱它。全世界250部最卖座电影中,其中246部是美国制作和共同参与制作的,只有4部是例外(英国的《光猪六壮士》、意大利影片《美丽心灵》、日本《千与千寻》和《哈尔的移动城堡》)。但这些美国影片有多少能直抵人心,让人产生共鸣?假象难以产生感染力。如果说这种无处不在的软实力有诸多影响的话,那它产生的厌烦感而非吸引力让人出乎意料,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硬币的背面。1960年代的欧洲学生运动导火索乃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1964年后西方学生运动狂飚。但矛头很快指向了美国,美国遭到反戈。
美国的形象总是与外界对它或美国政府的谴责相伴,这样有趣的现象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在2004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成百名示威者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来被警察驱散。电影《怪物史莱克2》的制作商在大街上放置了大量印刷有史莱克绿色大耳朵的袋子,为该片做宣传。示威游行者散去时,许多人顺手带走了袋子,人们喜爱史莱克的大耳朵,为它的傻气吸引。
越战后,美国文化渗透无处不在,这同样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软实力的怨怼。法国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感甚至强化到影响了国家决策。法国通过“杜蓬法”,使用英文单词将受到处罚。1993年法国劝说欧共体在贸易条款中增加了“文化特例”条款,豁免文化产品可或多或少不受通常自由贸易规则的限制,其他欧洲国家也不拘形式地对美国电视节目配额进行了限制。
欧美文学论文篇(5)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欧美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欧债危机 政治经济学 研究综述
一、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
(一)外部原因
从外部根源的经济因素来看,虽然考特赫里(Cottarelli)和谢克特(Schaechter)认为,欧洲国家债务水平总是在困难时期逐步上升,却没有在繁荣时期下降,因此债务危机是此前长期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结果,而不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但中国学者普遍将国际金融危机视为欧债危机的直接形成原因。宋国友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刘洪钟也指出,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触发器。两位学者将欧债危机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将之看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深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对此,扈大威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税收减少,资产泡沫破裂,迫使私人经济部门实行去杠杆化。在私人部门债务向公共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激增,债务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延伸表现形态。
从外部根源的政治因素来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王晓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其具有的广泛影响力,降级活动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余维彬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认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可能存在国家战略意图。但他并未就此继续探讨下去。黄河和吴兴唐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将这种国家战略意图的矛头指向美国。吴兴唐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推行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结果,目的是打压欧元,进一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河将这种霸权行为具体化,美国评级公司利用其“特许经营权”攫取了全球金融资产定价权,使其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通过这些大搞虚假评级的巨头不断扩张其经济帝国的霸权,三大评级机构也已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和金融战争的锐利武器。
(二)内部原因
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不禁发问:为何债务危机在被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最好的欧洲爆发?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威胁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从体系层次引向单元层次。在单元层次上,学者们主要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个是欧盟层面,一个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层面。
就欧盟层面而言,主要有“治理结构缺陷说”、“财政纪律缺失说”、“法律条款缺陷说”和“一体化过快说”等等。“治理结构缺陷说”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问题,85%的文章都提到了这点,即欧元区在实行统一“货币”时,却实行分散的财政政策。这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保建云认为,由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归属于欧洲中央银行,但欧洲央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大国,即法德等国家,而小国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何帆认为,存在“成本外溢”机制,其一成员财政扩张所引发的通胀成本将由经货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成本分担方式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但是,这种“赤字动机”是否必然导致小国就会大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了呢?欧盟在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对此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是否能够制约各成员国呢?“财政纪律缺失说”和“法律条款缺陷说”对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刘兴华回顾了近二十年德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后发现,2002年~2005年,德国均超过3%和60%标准,其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在2005年修改了《稳约》,给欧盟约束规则带了个坏头,也给其他国家违反规则找到规避的借口。周茂荣也认为,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财政纪律执行不力,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刘洪钟认为,《稳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一直是欧洲政策的核心,这项条款主要为了威慑和遏制成员国激进扩张的财政政策行为,但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最终采取了救助行为,违反了条款,也使其失效。部分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认为问题出在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由于成员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当年扩展过快过大。孙杰甚至认为,由于各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差异甚至扩大了。对于当时为何扩展过快过大的问题,丁纯认为,欧洲一体化更多地是由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的。政治收益的考虑超过经济收益是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从危机爆发的外因和欧盟层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治理结构的缺陷双重作用下,欧元区部分国家试图采取大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压力,并且,在表面上完美制度设计背后的监督松散性和法律条款的缺陷又使之成为可能,欧债危机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制度缺陷中爆发了。但这其中,仍旧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欧元区小国的政府税收为何得不到增加,政府支出又为何减不下来呢?学界对此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冀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层面。
在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特别是出现问题的南欧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竞争力”是所有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切入寻找原因,落脚点都是回答“为何南欧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也正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学者们对欧债危机的国内根源研究比较丰富,有“经济结构失衡论”和“选票绑架论”以及从中引申出的“高福利论”。
“经济结构失衡论”是学者们认为的国内根源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冯伸平认为,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魏民指出,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去工业化”之后,已基本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此时,虚拟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难免对一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为何在南欧国家得以确立呢?学者们进一步作了探究。虽然以德国为首的国家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主导经济模式,但是,南欧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来自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吴兴唐就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金融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近20年来,美国竭力向欧洲推行美式“新自由主义”,改变欧洲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内容,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逐步而深度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体系。陈凤英指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极致化。而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消极影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所以,在南欧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方面,学者们将其归结于英美经济模式扩张的结果。“选票绑架论”和“高福利论”从南欧国家民主制度中寻找原因,认为南欧国家的政治家处于选举需要,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增发福利、取悦选民。这种福利的增长把目标指向法德等发达国家,但经济实力却基于极大的不平等性。曲星认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零和博弈损害了公共效率,民主政治异化成选举政治,导致工资和福利过快上涨,从而引发危机。张建国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欧洲目前人口的老龄化严重,已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怪圈。来永红甚至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冯仲平将这种福利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下降联系起来,“维护高福利就意味着保持欧洲产品的高成本,其后果则是欧洲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方面,南欧国家的发展日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远高于自身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南欧国家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从这次学界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呈现逐渐全面和逐步深化的特点。对于任何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够研究透彻的,欧债危机的成因也不例外。虽然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完全遵循上文外部环境――欧盟层面――国家层面的逻辑,但是能够发现,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广泛的,每一位学者都试图回答既有文献提出的问题,或者既有文献忽视的方面,或者针对初步解释,通过研究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样,虽然,每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有限,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已经能够呈现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图谱,为以后学者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不断。以上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并没有包括所有学者的观点,不少学者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对既有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高福利经济制度是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戴炳然反问:为何社会开支最高的北欧国家受危机影响反而最小?对此,林德山、吴兴唐、王鹤等学者都对此作了回答,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福利制度管理出现了问题,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制度不相匹配造成的。再者,针对绝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治理结构缺陷说”,孙杰和孙少岩的两篇论文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杰认为,从表面上看,此次债务危机似乎印证了此前流行的有关欧元区制度安排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的观点,即欧元区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各行其是、不受约束,最终酿成了希腊的债务危机。然而,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也即是这一观点,将学者们的专注点从“欧元区治理结构”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欧元区制度的松散性。孙少岩则是通过与西非法郎区进行对比以及深入分析欧债危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后发现,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欧债危机的爆发。另外,刘程基于新三元冲突理论解释了其不赞成“过度消费论”的观点。这些学术争鸣使得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不断地运用新视角和迸发出新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的成熟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丰富。学者们在本次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包括霸权稳定论、霸权依赖论、权力转移论、公共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币缘政治理论和小国开放经济理论等。过去,对于问题研究,中国学者较少借用理论来做分析框架,更多地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根源,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观点的说服力。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既有理论解释中寻找原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当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缺陷或者无法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对理论进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一大进步。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懈努力。其次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性确实在逐步提高。
三、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分为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学者们对当前影响的研究,包括经济方面:冲击了欧洲金融业、拖延经济复苏、股市和汇市过渡动荡、通货膨胀。政治方面:极右翼政党崛起、疑欧主义发展、政府间主义力量加强、民粹主义泛起等等。由于当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欧洲主流政治和经济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因此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主要考察欧债危机对欧洲和全球产生的长远及重大的影响。
(一)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关于长远影响,首先必须回答两个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1)欧元区会不会?(2)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倒退?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西方,“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倒欧派”认为,欧元有最终崩溃的危险。他们甚至公开争论欧盟解体的可能性。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说,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相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几乎没有唱衰欧元区与欧盟的论调。学者们均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欧元不会,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倒退。何帆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而这不是希腊等欧元区小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学者从政治战略角度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比如,宋新宇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赵柯认为,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对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能使欧元区走向解体。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欧元前景的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思考的,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从政治角度来思考。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正如德国总理莫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者们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下的危机,认为,危机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大势总体依然向好,欧债危机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更深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这更深一体化应该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财政联盟道路。戴启秀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欧盟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不断克服危机、不断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这次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仲平认为,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先走一步,其他国家则等条件成熟后再跟上。他认为,“多速欧洲”是未来趋势。张健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他更精确地用“双速欧洲”指代欧元区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陈新、熊厚则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认为,欧债危机无疑将促使南欧国家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
(二)对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影响
在探讨了欧元区发展前景之后,下一步便是重新评估欧元在危机后的国际地位问题。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欧元的创建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那么,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欧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是否仍持这样的期盼呢?换句话说,欧元是否还有实力挑战美元?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未来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可以依据欧元是否还能对美元形成挑战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以高倩倩、郑建军和宋国友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此次债务问题,欧元仍然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多元货币格局将形成。高倩倩和郑建军认为,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还是相当温和的。宋国友认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王东则从反面美元地位的下降角度,认为,由于同样遭受信用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并不比欧元好到哪里去。魏敏同样认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实际是在为美元的最后挖掘坟墓。
悲观派以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为代表,认为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一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面前。他们认为,欧元从属于美元的结构将使其无法取代美元。乐观派与悲观派虽然表面上持不同态度,但实质上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一方认为很有可能,另一方认为难度较大。悲观派之所以更担忧欧元的国际地位,是其更关注货币的政治逻辑的结果。王湘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提出“币缘政治”概念后,货币的权力属性日渐为学者们所认同,并且“币缘政治论”在此次欧债危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湘穗指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的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由此可见,货币背后的权力才是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而权力最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样看,兰永海等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利用国际评级机构打压欧元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外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学者们也比较谨慎。李晓、冯永琦认为,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现行“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过激的“替代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切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币仍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个条件――稳定的币值、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高的透明度。张谊浩、裴平、方先明认为,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还有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打压欧元后,下一步将针对人民币。兰永海提醒我们,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三)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一轮关于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讨论又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金融危机期间,学者们热烈探讨了美国是否走向衰弱。而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欧洲是否正在衰退。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也不意味着欧洲势力的降低,世界仍然将走向多极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正在衰退,多极化将难以形成。对此,来永红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将形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零极时代”。而王义桅认为,世界将蜕变为两极化:美国代表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国家。
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权力分配方面,学者们均认为,(1)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相对上升。学者们为这一论断赋予了很多词汇,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的全球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等等。但同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2)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相对衰弱,并且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一论断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论断是相同的。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权力分配变化时,与2008年相同,较少有实证分析类的文章,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实力,绝大多数论文仍旧是策论类的,这导致此类论断缺乏科学性。在没有具体数据和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论断更多出于学者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影响,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隐性的债务问题。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否相对上升需要运用科学工具提供使人信服的数据和资料。否则,对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研究将仍旧模糊不清、深度有限,对于进一步的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就更难以进行下去了。
另外,学者们的推理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欧洲经济的衰弱就推导出欧洲正在衰弱,仅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发达经济体就推导出新兴经济体地位正在上升是欠妥的。一国的上升或衰弱是一种实力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从债务危机推导出经济衰退,进而推导出国家衰退的逻辑是不科学的。欧洲经济实力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其仍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其科学技术、政治模式、国际影响力、软实力等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欧美文学论文篇(7)
对于同一问题,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一般讨论的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和"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从笔者接触的文献来看,中国学者似乎对世界格局问题倾注了比别国学者更多的热情,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也较深。在有关讨论中,"多极"、"多极化"、"多极世界"、"多极格局"是用得很多的术语。中国学者基本认同现今世界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可用"一超多强"[3]来概括,未来将形成多极世界,而且作为国家集团的欧洲联盟(欧盟)堪称一极。
本文即是在假定当今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的前提下,评析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论述,然后以笔者所主张的要素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加以评估,最后提出对欧盟性质的认识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价
近些年来,在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4]的推动下,学界对欧洲联盟的研究不断加强。就对欧盟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关注的是欧盟对外政策及其国际影响、美欧关系、中欧关系、欧元的国际意义等,在对外关系研究方面的重点还是经贸领域。坦率地说,中国学者既有研究成果没有对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进行研究性的、量化的定位。这可能与欧盟迄今为止还主要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学界对欧盟的国际影响还是寄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是"在欧洲和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力量"[5],"欧盟作为在国际上正趋上升的力量,其变化将是今后国际局势中极为关键的因素"[6]。笔者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假定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一种正在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的话,欧盟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于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学者给出的多是定性的论断而非分析。如果加以分类的话,则会发现这些论断实际上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欧盟要在世界格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二是欧盟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三是一体化的欧盟将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关于欧盟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设定,中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欧盟成员国会在认识到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解决发展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欧洲联合,欧盟将谋求发展成为一支对美国具有平等地位的独立的超强力量,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7]换句话说,欧盟希望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强大的一极"。[8] 在中国学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实力的增强是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有力因素。
其次,就欧盟在现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来说,中国学者的看法有所差别,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欧盟已经是重要的一极,如:"在冷战后的多极格局中,西欧作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断上升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强大的一极","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盟都已是确定的强大的一极,以一极的身份和地位对世界事务实施着影响"[9];"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来看,今天的欧洲联盟已成为冷战结束以后多元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欧洲联盟已成为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同样重要的国际力量"[10]。另一种观点认为欧盟的国际影响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现今还称不上一极。由于"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联盟","欧盟在迄今为止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尚未显现,特别是欧盟企图联合起来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的计划也没能落实"[11];"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从欧洲的一极上升为欧洲最强的一极,再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的一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
最后,对于欧盟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中国学者也是在确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的前提下作出论断的,基本观点极为相似,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欧盟终将作为重要的一极出现在今后的多极世界中"[13];"随着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显得更加突出,并将成为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14]。
在对现今的世界格局或者构成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中心进行具体分析时,中国学者大都把欧盟作为多极化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例如,沈骥如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五个极,即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个极的力量并不相等,只有美国是一个完整的极"[15];郗润昌则认为"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美欧日俄中五大力量即五极支撑的新格局雏型"[16];而在陈德民看来,当今世界多极化是既定趋势,表现在"一超多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个力量中心,如美国、日本、中国、欧盟、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17]
中国学者把欧盟看作推动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根据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欧盟的综合实力及其日渐增强的独立性。欧元启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成,作为政治一体化核心内容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防务政策建设也不断取得进展(科索沃战争大大推动了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步伐),被认为展示了欧盟要"控制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动权"并"成为国际政治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的坚定决心"。[18] 在分析欧盟的综合实力时,一些学者更喜欢引用欧盟经济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如把欧盟内的生产总值近些年来超过了美国,而且欧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超过了美国和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等等看作欧盟成为一极的资本。他们对国际舞台上欧盟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乏力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不过,也有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欧盟在国际上主要发挥着经济作用,"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并实际运作以前,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十分有限"。[19] 此外,一些学者还把欧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和独立性以及欧美之间的摩擦看作欧盟谋取一极地位的表现[20],有的甚至希望欧盟成为"制衡美国霸权行动的有效力量"。[21]
二、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估
一般地,我们把世界上大的力量中心作为格局中的"极",这样的认识依据的其实是它们的综合实力。但世界格局要真正形成,还必须由这些力量中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最后定型。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即是在美国和苏联一系列战略政策互动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当然其核心的决定因素是两国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假定现在存在着多极化趋势,那么多极格局最终也需在有关力量中心互动并建立起较为稳定和相对平衡的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形成。
评估"极"的要素设定
在笔者看来,判断一个力量中心能否构成世界格局中的一"极",需要对有关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进行综合的考量。具体来说,一个力量中心要成为"极",至少应具备以下要素:
1. 强大的综合实力。这是与其他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结构状态的决定性条件。实力是基础,一个小国虽可凭出色的外交纵横捭阖,但若没有足够大的综合实力,是不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恐怕没有人会把韩国、新加坡甚至加拿大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极"。
2. 成为一"极"的意志和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这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一个力量中心以实力为基础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定位决定了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其意志和政策的执行将引起世界上其他力量中心的互动反应。二战结束后,如果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而不是对抗苏联、谋求建立和维护其霸权地位,两极格局不可能很快定型。就中国来说,冷战后期能充当大三角中的一角,仅凭当时的国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美苏当时的相应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虽然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地区性大国[22],但由于中国具有强烈的成为大国的愿望并有相应的战略措施,中国能够在世界格局的型塑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3. 较强的外交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也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被称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怀疑美国作为一"极"的地位。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除美国外,尚无真正称得上一极的其他战略力量"。[23]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较为局限,所以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一"极"。
4. 外部世界对其地位的普遍认同。这也是成为一"极"不可缺少的条件。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接受和认同,它也很难成为有影响的一"极"。构成世界格局的大的力量中心都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逐渐为有关国家接受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发挥较大的影响,除了自身的实力和政策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法、俄等国的认可。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国的判断和政策。
倘若以上述要素来判断当今世界的力量对比,我们会发现美国是综合国力最强大、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企图和战略明确、国际影响力最广泛、既有国际地位得到无可置疑认同而且任何其他力量都无力根本地对之挑战的力量(虽然世界上很多事务美国无法单独主宰),的确是最强大的一"极"。俄、日、中、欧等与美国相形逊色。
对欧盟作为"极"的条件的评估
下面,我们以上述四个要素为指标,来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成为一"极"的条件加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很多内容无法量化,笔者这里的分析也主要是定性的分析。
首先来看欧盟的综合实力。若单单从欧盟15国整体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资源来看,地理面积323.5万平方公里、人口3.7亿、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GDP 88100亿美元(1997年,同年美国GDP为75230亿美元)、有两个核大国(英国和法国,两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科技教育发达的欧盟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力量。[24] 不过,由于欧盟不是像国家那样的体制,其内部整合程度还不是太高,理论上讲其实力很大,但在实际运行上则受到体制、成员国内部利益矛盾和政策差异的限制,所以在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进行评估时,应对其简单相加的而非整合起来的实力大打折扣。我们很多学者正是把欧盟表面上的强大实力看作其可实际运用的力量,以此判断欧盟的国际地位,作出过高的估计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分析欧盟的国际定位和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行为体。中国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欧盟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世界格局一极的角色,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国际作用。笔者认为,欧盟的确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确实希望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欧盟现在对自身的定位主要还是寻求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是充当一极。在欧盟条约、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中,我们看不到欧盟对充当多极中一极的企望,而只是要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欧洲联盟身份"[25],其政策重点是推动内部的政治一体化。当然,基于欧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在政治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能够真正施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防务得以建成的条件下,欧盟应会对自身的国际作用提出更高的要求,追求世界格局一极的位置也是应然的。但就现在来说,欧盟还没有把自身定位于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倒是法国赞同世界格局多极化并积极推动这一发展趋势。而且,由于欧盟不具备国家那样的地位和意志,15个成员国利益和政策主张各异,欧盟很难整合出一套统一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措施。[26]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而且与美国有着传统的伙伴关系,同在西方阵营且有一系列的机制(八国首脑会议、北约等)将它们绑在一起,很难设想欧盟会与美国完全对抗。欧盟最多希望成为美国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平等竞争者。
再次考量欧盟的外交力和国际影响力。欧盟虽然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框架和一系列措施,但其施行仍很乏力,无甚大作为。在海湾战争中,欧共体成员国对外表现出来的是各异的立场和政策。对于波黑冲突,欧盟虽寄予充分关注,希图独立地加以处理,然而由于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欧盟成员国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反而政策各异,无法共同行动。其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经由阿约有所发展,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再次考验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实践证明欧盟尚无能力推行统一的对外政策。这些事例都表明了欧盟现有政策措施的根本缺陷和外交力的匮乏。这种情况在被认为充当一极角色的其他力量中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就国际影响力来看,欧盟在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较强的影响,欧元的启动大大提高了欧盟的地位,在这些领域,欧盟的影响要比俄罗斯和中国强很多。欧盟还通过《洛美协定》[27]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无可比拟的。但在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欧盟至今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其影响力有限。实际上,决定一国能否成为一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在"高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俄罗斯的地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其经济近10年虽严重滑坡,但在全球战略力量对比中的地位依然重要),而这些领域正是欧盟现有能力所不及的。
最后考察外部世界对欧盟国际地位的认同程度。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卓著的区域性组织,欧盟一直被世界其他地区视作一体化运动的范例。而且欧盟作为成员国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得到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认可。欧盟与世界上大多数第三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向这些国家派驻了使团。在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欧盟都具有重要的法人资格。但就现今来说,由于欧盟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他国家和组织之所以与欧盟打交道看重的是其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而不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28] 也就是说,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欧盟的国际地位还没有为国际社会充分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学者非常强调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但在中国对西欧的外交实践中,却更重视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与欧盟本身的关系。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欧盟的地位还没有为中国所认同。
综上所述,欧盟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还称不上一个完整的极,甚至不如日本的作用突出。日本虽然也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其作为国家一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其在国际定位、外交力、影响力以及国际上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都比欧盟强。把欧盟看作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核心力量之一是有欠全面分析的。但也不可否认,欧盟作为区域化力量的突出代表,其发展有助于多极化趋势。当然,我们讨论世界格局多极化并不是说几大力量中心的实力是完全均衡的。如果我们要对世界格局中的几大力量中心进行排位的话,笔者会把欧盟看作是中国学者所接受的五大力量中心中最为蹩脚、行动能力最差的一"极"。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未来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做一粗略的展望。未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继续深化和扩大,尤其是政治一体化的推进,欧盟的超国家性将加大,欧盟的综合实力和行动能力将会不断加强,欧盟也将取得对美较大的独立自主性,欧盟在世界格局中发挥比较大的、相当于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作用是可能的。
三、对欧盟性质的认识
在考量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欧盟的性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欧盟的独特性有充分的把握。对于欧盟的性质,欧盟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
对于欧盟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国际行为体身份这一论断,中国学者应是接受的。当我们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来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欧盟看作了一个国际行为体。传统上我们只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二战以后学界基本认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等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欧盟是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区域组织,可称为"国家联合体"而不是国家。不过,欧盟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对于邦联这样的松散的国家间的联合,欧盟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在成员国自愿让渡部分(如对外关税的制定、贸易政策、缔约权等)并形成集体行使这些权力的独特机制的基础上,欧盟得以建立并已建构了一些具有超国家性的独立于成员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如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行使原由成员国行使的部分国家职能(具有一些超国家权力),并形成了一套有很大效力的欧洲联盟法,具有了联邦国家的雏形。不过,欧盟的职能范围和行使方式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
对于欧盟的性质,学界从研究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出发进行了诸多讨论,但并无统一的明确表述。中国学者戴炳然称欧盟为"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并具体论证说欧盟"具有鲜明的超国家特征",是"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一种体制","多元复合的体制"[29],也有人认为"欧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一种介于联邦制联盟和邦联制联盟的混合制结构,或者说仍然是一个具有一定联邦性质的联盟"[30]。这样的表述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欧盟的现实性质,但又未免过于罗嗦,定位也不明确。在现有的语汇中,还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定位欧盟的性质。笔者曾主张把欧盟视作一个具有很强超国家性的独特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仔细思考这一表述仍然太长,而且对欧盟体制的发展取向没有涵括。
西方学者也认为要准确描述欧盟的性质特点有些困难,不过他们还是进行了理论上的尝试。纽金特认为欧盟作为一种政治体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称不上一个国家,但又比政府间组织程度高得多"。[31] 在拉吉看来,欧盟是一种"多维政体"("multiperspectival polity"),是"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国际性政治体制"("the first truly 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rm")。[32] 卡波拉索则称欧盟为一种"后现代政体"("post-modern polity")。[33] 应该说,把欧盟看作"后现代政体"的说法抓住了欧盟的复杂性,并能反映其多形结构(polymorphic structure)。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两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试图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来描述欧盟的性质都是徒劳无功的。[34]
以笔者管见,用"后现代政治实体"(a postmodern political entity)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来定位欧盟还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能充分反映欧盟体制的独特性,从中还可体现欧洲民族国家的不足、冷战结束带来的特殊机遇和期望以及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的发展。而从国际层面上讲,作为一种后现代政治实体的欧盟已超越了一般的非国家行为体,但还不是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也许只能说是一个准国家行为体。
欧盟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较为特殊的作用,也决定了其行动能力的受限性、位置的薄弱性。欧盟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但它的政治作用还极为局限,在关键问题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施行还软弱无力,建设共同防务将是一个艰难的、长远的努力目标,而"防务是共同体在世界上位置的关键"。[35] 就现在来说,欧盟依然是一个"民事力量"而不是一个"超强力量"。[36] 虽然欧盟的成员国有着相当大的实力,但作为整体的欧洲联盟的实力却很有限。不过,随着"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安全的内涵渐渐扩大,欧盟将来在国际舞台上应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37]
四、对有关问题的评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希望对与本文论题有关几个问题给出简短的评论。
一是中国学者判断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取向。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反过来官方的政策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有关的研究。中国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视作一极,这一立场影响了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判断。中国学者对欧盟的国际作用估计偏高并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暗含着他们对欧盟未来角色的期望:欧盟的强大有助于多极格局的形成,欧盟将对美国产生制衡作用,这样形成的世界格局对中国有利。
假定欧盟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它与美国会相互制衡吗?欧盟能成为反霸的力量吗?的确,冷战结束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和磨擦,欧盟还希望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但这改变不了它们之间的集团或同盟关系,北约的框架将继续主导欧美关系。最根本地,它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同质性的,而且都是市场民主国家,这就决定了欧盟未来虽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但欧盟和美国不可能闹翻,它们不会成为相互排斥的对手。对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盲目夸大。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即使将来形成多极世界,也不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各相制衡的结构,西方国家仍将是一个整体。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宾尼恩迪克在分析现今国际体系时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多极状态,但国际体系最终可能会走向危险的两极,即西方对非西方的格局,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会与所谓的"无赖国家"加强合作对抗西方。[38]
二是中国对欧盟的战略选择。在对待欧盟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让人困惑。一方面,中国强调多极化,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作为一极并强调其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政策中,中国没有把作为整体的欧盟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甚至对欧盟的重视还比不上对单个成员国的重视。这与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普遍高估形成反差。对此问题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多极化战略出发在多极化问题上把欧盟看作一极,但实践中欧盟整合力的欠缺、行为能力的局限性又使我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重视与欧盟的经济关系,重视对欧盟成员国中大国的传统关系,而不看重与欧盟的关系。这样的政策虽然可行,但却难以充分维护中国的利益。
欧盟在中国实际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较低。笔者认为,中国除了要在多极化问题上看重欧盟之外,还需要从全球战略的高度重视欧盟,形成明确系统的对欧战略,提高欧盟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这不是抬高欧盟的地位,而是现实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政策上的需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欧盟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现在欧盟的整合力还比不上美国,但在战略上重视欧盟,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如果把欧盟放到一个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将有利于我们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至少可以增加对美外交的砝码。总的来说,在战略上把欧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对长期趋势把握和现实政策需要综合衡量的理性选择,会有助于增进中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中国对欧盟的研究。依笔者之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重视并加强对欧盟的研究。在对欧盟进行研究时,不应围着政府的定论转,而应进行深入的历史、现实分析,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并了解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以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客观世界。中国学者高估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与中国的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欧盟研究的滞后。在2001年7月份的"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趋势与新视野"国际研讨会,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老前辈陈乐民先生批评了我国有关研究中存在的"重美轻欧"现象,提出应把欧洲问题研究当作一项学术事业来进行,从而使研究向深入、细致方向发展,进而建立中国的欧洲学。这是中国欧洲问题研究学者今后需认真记取的。
注释:
[1] 在讨论"世界格局"时,学界的话语并不统一,有的也称"世界政治格局"、"世界战略格局"、"国际格局"、"国际政治格局"。无论哪种说法,中国学者关注的都是政治格局。一般地,"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或说对比状态。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 耿殿忠:"简析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0期;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潘维:"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与世界格局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4期;严基河:"当前世界新生格局辨",《世界知识》1992年第6期;孟祥青:"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载顾德欣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2页;程林胜:《大变动的世界格局与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卢静:"浅谈20世纪国际格局的变迁",《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郗润昌:"世界政治多极化与新格局框架",《学习时报》2000年7月10日第2版。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即就世界格局判断问题进行过诸多讨论,具体情况参见刘海军:"我国关于多极(化)格局的两次争鸣",《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第41-45页;中国学者在多极化问题上的分歧亦参见俞邃:"认识多极化,促进多极化",《当代世界》1999年第9期,第12-14页。
[3] 多数学者赞同"一超多强"呈现出的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个"美国单极主宰的格局"。参见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3页。
[4]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 这是欧盟为推动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加强中欧学术和人员交流而拨资975万埃居支持的一个为期4年的项目,将于2001年10月结束。迄今为止,该项目向452位中国学者提供访问欧洲和37位欧洲教授访问中国的资助,批准了150个合作研究项目和35个课程开发项目,还召开了33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讲习班。
[5]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34页。
[6]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当代世界》2000年第2期,第13页。
[7]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和平与发展》1999年第2期,第45-48页;伍贻康:"面向21世纪的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二)",《欧洲一体化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1页。
[8] 高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进展",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
[9]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第36-37页。
[10] 宋全成:"论欧洲联盟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前景",《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40页。
[11]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第55-56页。
[12] 张祖谦:"欧洲三极格局的形成、现状和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40页。
[13]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第14页。
[14] 陈朝高编著:《欧洲一体化与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5] 郑园园:"我们追求的世界格局--关于多极化问题的访谈",《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6日第7版。
[16] 郗润昌:"多极化≠大国力量的均衡化--再谈多极化与新格局相关问题之我见",《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13页。
[17]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1期,第4-9页。
[18]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第7页。
[19]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第56-57页。
[20] 郭震远:"未来十年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展望》2000年第1期,第2-6页。
[21]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第48页。
[22]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亚太地区性大国,但却具有全球性影响。
[23] 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第123页。
[24] 亓成章、何中顺:《时代特征与中国对外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8页。
[25]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条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210页。
[26] 欧盟在经贸领域基本上施行了统一的对外政策,但在政治、安全、外交领域还未能实现统一的政策。
[27] 《洛美协定》期满后,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和地区于2000年6月签订了为期20年的新协定——《科托努协定》。
[28] See Elfriede Regelsberger, etc. (eds.),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15.
[29] 戴炳然:"欧盟: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上)",《欧洲一体化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8页。
[30] 赵伯英:《欧洲一体化的动力、矛盾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31] Neill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4th edn., Hampshire: Macmillan, 1999, p. 497.
[32]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1993, p. 172, 140.
[33] John Copora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forms of state: Westphalian, regulatory or post-moder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1996, p. 47.
[34] Charlotte Bretherton and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37.
[35] Christopher Hill, "The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or conceptualising Europe's international rol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3, p. 318.
[36] Curt Gasteyer, An Ambiguous Power: The European Union in a Changing World, Gu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Publishers, 1996, pp. 12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