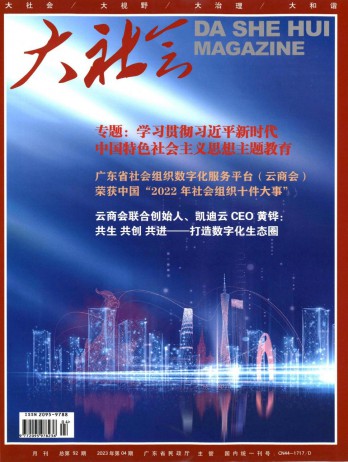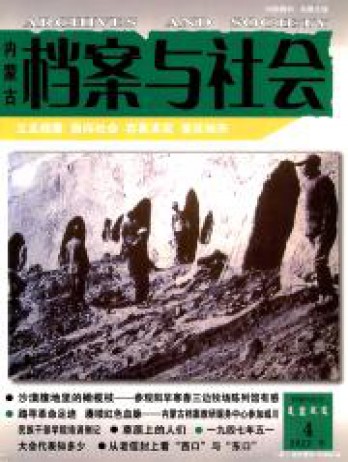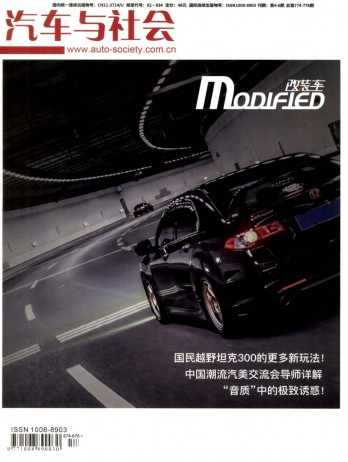社会变迁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11-18 14:16:30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变迁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思维范式
吉登斯在评价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这里的“另一相关研究”,就是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在评价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时,他说:“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在吉登斯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前一阶段主要反思经典社会思想和当代主要社会思潮,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后一阶段主要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结构化理论为后者即现代社会变迁提供理论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某种螺旋式的轨迹:它的一般原理融会贯通地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的构成的实质命题之中,而这些实质命题又反过来充实、推动了结构化理论更为抽象的主张的发展”。
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正如他所说的,“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我们只有在理解结构化理论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对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谓结构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化就是在绵延的行动流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反复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就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后果。正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社会的宏大结构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二重性是作为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通俗地讲,所谓“二元论”,是把行动与结构当作外在的两种东西;所谓“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吉登斯认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是结构化理念的关键”。因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旨在具体诠释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如何被消解于实践之中,而这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题。
结构二重性原理的内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来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总体来看,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概括起来讲,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又是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条件与中介,这要求人们从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吉登斯提出:“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不是片断式的,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社会生活川流不息,循环往复。因此,社会实践具有循环的特性,而结构二重性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循环特性。
第二,结构与行动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而共存的。结构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动之物,结构只能透过行动在时空里展现出来,它存在于时空之外。结构(规则和资源)被不断纳入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并跨越时空限制,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践而不断再生产出来;考察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意味着探讨规则和资源如何在行动者的行为互动当中实现再生产。另外,从行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也利用了社会情境中包含的丰富多样的规则和资源,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等书中,吉登斯还将结构二重性与语言(1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关系作了一个类比。他说:“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空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语言的结构存在于并通过言语行为而存在,并且使言语有了条理,而离开言语的抽象的语言结构是不存在的。与此类似,结构也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实现并使互动过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这一论述,明确了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之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深刻地揭示了结构的特性以及结构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第三,结构既具有制约性又具有能动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确地提出这条原理: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都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这就是说,结构在构成行动媒介的同时,同时也构成对行动的制约,而且这种媒介和制约关系还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反复被再生产出来。具体而言,从结构中的规则来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资利用的建构性因素。从结构中的资源来看,它也不仅仅是对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还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活动的可能空间,充当主体活动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思维范式
所谓“思维范式”,主要指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范式就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体中,它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他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更深层次的范式。本文在这里所讲的思维范式也是侧重于后一意义来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即实践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也被解读为生成性思维范式。吉登斯认为,社会与自然不同,人类虽然社会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类生产出来,不是人类行动的创造;社会尽管也不是由任何单个个人创造,但是它由每一个社会参与者创造并重新再创造出来,它“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是预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迁而转变。
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是对古代实体性思维范式和近代主体性思维范式的扬弃。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实体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所谓主体性思维范式,是将主体作为其理论的最终的支撑点,人的理性成为支撑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点”,这一思维范式是与近代以来人类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即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存在,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人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的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正是以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为指导的。正是基于此,他坚决反对社会进化论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构成性作用,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基于先验的动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他看来,自然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发展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觉的过程,根本无需人的参与,如四季更替、天体运行、地震海啸、花开花落等等,都没有预期目的,只表现为有一定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则离不开人,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社会的基础,而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因而,社会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最基本和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任何社会变迁都是极其随机性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被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现代社会变迁更加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他说:“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与其结构化理论所蕴涵的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认为,以往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之所以陷入认识误区,与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关系。客体主义者所使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孔德认为,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但在本质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服从普遍的因果规律,所以,应该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吉登斯批评指出,人类社会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实证主义方法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只是社会现象的外在联系,而不是社会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与客体主义者不同,主体主义者使用的则是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们主张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作如下区分:自然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事实知识,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价值知识。价值知识是指导人们行动“应该如此”的普遍性规范原则,它在人们行动中起着导向作用。吉登斯认为,人文主义方法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异质性,强调人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因素,反对把人当做非人格的社会存在物,这是可取的。但它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结构对行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完全抹杀了。
吉登斯则以实践的思维范式为指导,扬弃了上述方法,提出了“双向阐释”(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双向阐释”是指,一方面,社会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大众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反馈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的活动范围即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去,社会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本身。这些知识、概念和理论,对它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人们根据这些知识对自身行动进行改造和调整(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这些知识不断卷入现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的过程。但因为人类行动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在现代社会,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些不可靠的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现代社会,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驾驭的风险社会。
四、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内容与结构具有内在的关联
篇(2)
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篇(3)
论文摘要:卡尔·贝克尔,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史学的代丧人。((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是贝克尔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光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
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I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己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噢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
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沦域的礼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肩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足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白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二)启蒙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篇(4)
关键词:农村; 体育; 研究
一、农村体育研究现况
(一)概念界定
相关农村体育的基本概念主要体现于对"农村"、"农村体育"、"农民"、"农民体育"及"村落体育"的认识上。
1.村落及村落体育概念的界定
村落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最主要的自然聚落,具有社区的社会关系、秩序以及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村落的边缘清楚,由固定的农业人群长期聚居和生活所组成的空间和社会单元。
村落体育是指在村落环境中以村民为主体,以健康、娱乐、休闲等为目的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属于社区活动概念,具有文化层次含义,包括各种现代体育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2.农村、农民及农村体育的界定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居民聚居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主要场所。
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人群才能称为真正的农民。
农村体育是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
(二)农村体育组织研究
当前村落体育组织结构松散,缺乏稳定性。有学者从自组织理论出发,分析农村体育的历史变革与农村体育组织演绎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组织演进是当前农村体育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应明确自身角色并合理定位。
(三)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主要涉及体育人口、农民体育意识和态度、体育价值观念、健身场所、锻炼时间及地点、活动内容等方面。现状反映出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体育发展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村体育管理上存在以"城市体育"衡量农村体育的惯性思维,发展理念上与本土体育及乡土实际的背离;地域范围内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农村体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村体育组织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理念、文化等方面。
(四)关于农村体育对策的研究
在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相应的建议。朱勇从村落体育的善本再造角度强调"原生态"价值取向对村落体育和农村体育的重要性,指出在继承、发扬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掘传统体育的同时,推动农村体育的多元和文化和谐发展。郭修金从小康社会的建设为视角,认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向下进行转移,县城是农村体育的龙头,乡镇是农村体育发展的纽带,村落是农村体育的根基和落脚点,强化政府职能,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合理发挥。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概念界定不清
由于社会的飞速变迁,对农村、农民、农村体育的界定存在模糊,给相关研究带来瓶颈。由于关于农村体育理论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必要性,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对农村体育范围进行界定。
(二)农村体育研究边缘化
我国对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虽然近年来全面健身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进展,但从国家社科基金和体育总局软科学理想资助情况看,农村体育只占3.67%。此外,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容易站在现代体育的视角来审视,忽略了农村社会变迁发展的现实,与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
(三)研究对象不清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中的"农村"范围过大,对所辖行政村即自然村落社区的体育活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村落是地缘和血缘关系醇厚农村的主体,较多地存在着依靠农耕的完全意义上农民,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也正是起源于村落以及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而这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亦可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并对与现代体育的结合和推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四)研究方法偏失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共时性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经济、有效地获得研究者所需的调查资料,但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频繁,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容易影响到问卷效度和信度,一个时点的共时性问卷调查不能反映出农村体育发展全貌。
三、结语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体育研究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但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两者结合脱节。农村体育的研究应把握"农村"的实质,与当地的民俗、地貌特征、经济发展、文化习惯、传统体育等结合,不能追求公式化;应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运用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农村体育,站在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体育。
参考文献:
何肇发.社区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罗湘林.村落体育研究.北京体育大学,2005.2005.罗湘林.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体育科学,2006(4):86-95.
郭修金,虞重干.村落体育的主要特征与社会功能探析--山东临沂沈泉庄的实地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7,27(3):33-36.
韩明谟.农村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吴振华,田雨普.关于中国农村体育若干问题的断想.体育文化导刊,2005,36(5):5-6.
卢元镇.社会体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卢元镇.社会体育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3.
陈安槐,陈萌生.体育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张红坚,段黔冰.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2):20-22.
韩军,王斌,马红宇.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思考.体育文化导刊, 2009(6): 16-20.
奚凤兰.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我国农村体育.体育文化导刊, 2006(9): 8-10
篇(5)
>> 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 基于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翻译语言分析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服务平台建设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酒店英语语言特征研究 浅谈语料库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 基于语料库的认知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词汇语法研究 基于语料库方法的郑渊洁童话“儿化语言”特色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应用语言学方向论文摘要研究 基于类比语料库的中国新闻英语语言特征研究 基于FAO语料库的农业英语语言特点研究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英语课堂话语研究评述 基于语料库的《典仪》的检索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唐朝的酒文化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词语搭配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influence搭配行为对比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语篇分析范式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写作测试效度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医学英语介词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公示语“厕所”翻译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的工作指南:
(9)a.Respond as a reader, explaining what and how you were/are thinking as you read her texts so that she can discover where a reader might struggle with her writing.
b.Ask him to outline the draft to reveal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aper.
c.Ask her to describe her purpose and audience and show how she has taken them into account in her writing.
d.Explain a recurring pattern and let him locate repeated instances of it.
译文:
a.回应读者,解释当你读到她的文本时你在想什么,以便她能够发现读者在什么地方和她的论述发生冲突。
b.要求他提出大纲以便显示论文的结构。
c.要求她描述她的目的和她的听众,说明她在她的写作中是如何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
d.解释重提模式,让他找到模式中重复的例子。
这个极端的例子中,为了避免片面地使用人称的阴性或阳性,采取了交替使用“he”和“she”的方法来保持性别的失衡。
2.避免使用人称代词回指语
还有一种指称的语用变异现象,就是为了避免语言歧义而彻底清除人称代词。例如:
(10)Allan Johnson is a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ist.This writer and professor gave a speech at UNC in the fall of 2007.
译文:艾兰・约翰逊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这位作家兼教授在2007年秋季在UNC举行了一次演讲。
这个句子中,Allan Johnson的同指语没有采用常规的代词回指形式“he”,而是使用了名词形式“This writer and professor”作为回指语。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补充新信息,二是避免使用阳性的指称形式来指称这位“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学家”。
3.两性人称代词回指语并用
在新闻英语的语料中,出现了大量使用“he or she”“she or he”“he/she”或“she/he”等两性并用的代词形式来表示泛指概念。对BNC语料的统计显示如下表:
英语人称代词词汇变异频率对比
例词 口语 小说 新闻 学术 文娱
数量 频率 数量 频率 数量 频率 数量 频率 数量 频率
he or she 57 5.7% 40 2.5% 60 5.7% 555 36.2% 1009 22.6%
she or he 2 0.2% 0 0% 0 0% 18 1.2% 34 0.8%
统计结果显示,完全形式“he or she”和“she or he”主要用于政府公文、法律文件中;而使用“he/she”“him/her”“him/her”等变体形式只偶见于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中。无论是完全形式还是缩写形式,都是以阳性先于阴性的形式为主。这体现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另外,这种现象也可能和语言的韵律形式有关,因为“he”的音节要比“she”短,拼写形式也更简单。另一方面,“she or he”的出现也反映出一部分女权主义者意识的觉醒。这种语言变体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顺应社会变化,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意识,也有的是出于学术上或者法律上的严谨。比如当谈论的是和生理或者社会权益等问题有关的话题时,“she/he”或者“she or he”出现的频率往往比较大。例如:
(11)A student attending a well directed breast clinic may personally see this number of patients in less than a month and be taught to make an accurate clinical assessment.She or he would have to spend a year in general practic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similar skills.
译文:学生参加管理出色的乳腺癌临床学习可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亲自见到这个数的病人,并学习作出准确的临床评估。她/他通常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实习以便有机会学会类似的技术。
就目前所搜集到的语料来看,“he or she”和“he/she”的形式并非偶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现象,它实际上已经逐渐进入了主流语言之中。目前,语料库中“she or he”或者“she/he”这类样本量还很小,还仅仅是初露端倪,但还是可以从中透视出社会变迁的痕迹。
这种语言的变异表明,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语言中体现的性别歧视受到批判,因而采用可以兼指阴性和阳性的复数形式“they”来取代阳性代词“he”,或者采用“she or he”等形式以抵制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
在当代英语中还出现了语言“跨性别”(trans-gender)现象,即由于变性者的法律地位而引发的指称语的社会变异现象。例如,在一则关于世界首例变性“爸爸”生育的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
(12)If he/she wants to be a man, that is fine with me.If he/she wants to be a woman that is fine with me.But this is crazy how much publicity this story is getting.He/she is only doing something that women have been doing for eons, but getting much publicity for it.This individual is either very mixed up emotionally so that he/she can not make a decision on which sex she wants to represent and thus is more to be pitied than made to be a hero.
译文:如果他/她想当个男人,对我无所谓。如果他/她想当个女人,对我也无所谓。但是荒唐的是这个故得如此兴师动众。他/她不过是做了一件女人们做的异装癖的事,但是变得如此引人注目。这个家伙在情感上太混乱了以至于他/她无法决定她想当哪个性别。所以与其说是一个英雄不如说是令人可怜。
上面的例句比较典型。在这个语篇单位中,一系列的指称代词都使用了“he/she”,只有末句突兀地使用了一个阴性的代词“she”,用来突显“她”的真实性别,也表明了作者对“他”的否定态度。可见,在社会语境中,人称代词的指称功能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对名词的替代作用和语篇的衔接功能,它还具有了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
四、结语
从社会语境来看,人称代词作为语篇回指语时,不仅具有替代和衔接功能,可以作为认知状态的可及性标示语,而且还承载了社会功能。这种社会语言变异现象折射出变迁的社会权利意识,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言语群体的社会意识,浸染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文化色彩。人称代词指称的社会变异现象从一个微观的层面验证了语言的“异质有序”性,也启示语言研究需要克服传统研究中机械的、静态的、局限于形式化的研究路径,以动态的、全境的视角,以综观的方法论,从共时和历时的纬度来研究社会语境中的语言现象。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9YJC740021]和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0E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受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HEUCF121204]资助。)
注 释:
①anaphora一词源于希腊语anaphorá,意为“提起”或“唤回”
(carrying back or referring back)。在汉语中,anaphora除被译为“回指”之外,还被译为“上指”“前指”“复指”“指代”“照应”“参照”等。
②BNC语料库是世界上最大的英语语料库之一,词汇量达10亿左右,
时间跨度覆盖了20世纪后半叶至今。语料来源包括新闻、学术期刊、小说、书信、法律文书、政府和学校文件等,其中新闻语料主要源于国家和地方报刊杂志。
③Sinclair抽样提取索引的做法是该词语在语料库的频数除以要求
的索引行数,获得索引行抽样的间隔。如某一词语的原始频数为5000,如需要提取25行索引,那么,5000/25=200,即分别抽取第1行,第201行,第401行等。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 & Hasan,R.Cohesion in English[M].London:
Longman.,1976.
[2]Lyons,John.Semantics.Vol(2)[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 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篇(6)
【论文摘要】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现今中国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国际市场,西方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无不渗透到当今我国消费市场,而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等原因,符号消费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一、消费的符号化
现代社会将人置身于一个消费世界.社会内在的商品交换法则则是人们生活在这一世界的“黄金法则”。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指我们对物化的商品的消费。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的发展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
消费的表现性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物理或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而且是象征层面上的消费,即“象征消费”。象征消费指的是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关于符号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须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浪费,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凡勃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上层阶级出于阶级分野意识与标新立异欲望总是企图拥有一种明显的风格.如社交形式、衣着服饰、美学判断的标志与其他群体分开。而中间阶级的成员出于拉平化的本能尽可能地去模仿这些风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不同群体之间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他们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与认同感。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布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提到了在消费社会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档””中档””低档”似乎是在指物的分类而实际上是指人的关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费符号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中消费的符号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消费;符号化;符号消费
【论文摘要】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现今中国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国际市场,西方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无不渗透到当今我国消费市场,而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等原因,符号消费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一、消费的符号化
现代社会将人置身于一个消费世界.社会内在的商品交换法则则是人们生活在这一世界的“黄金法则”。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指我们对物化的商品的消费。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的发展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
消费的表现性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物理或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而且是象征层面上的消费,即“象征消费”。象征消费指的是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关于符号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须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浪费,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凡勃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上层阶级出于阶级分野意识与标新立异欲望总是企图拥有一种明显的风格.如社交形式、衣着服饰、美学判断的标志与其他群体分开。而中间阶级的成员出于拉平化的本能尽可能地去模仿这些风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不同群体之间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他们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与认同感。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布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提到了在消费社会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档””中档””低档”似乎是在指物的分类而实际上是指人的关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费符号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中消费的符号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快速、低价、包过!就找论文天下!
虽然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人对于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推崇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符号消费在我国消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以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豪宅为人生目标的人大有人在。并且这些都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社会标尺。
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不仅追求物质商品的符号意义。而是开始重视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等非物质商品,如休闲方式、流行音乐等。正是因为如此循环,进一步使得物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意义纠缠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使得人们对使用价值和物的符号意义的追求永无止境。
(二)空间的符号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伴随着人们新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诞生了一系列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场所(它们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如KTv、网吧、咖啡厅、KFC、超级市场等等,以及在旧形式下赋予新的消费符号意义的消费场所。如茶馆、酒吧、发廊、桑拿洗浴房等。这些新兴消费方式和场所的诞生和变化反应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几个典型例子做出分析。
在大中小城市中,各类型的超市见缝插针地深入到街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的大卖场、超级市场到处都是。这些超市有着非封闭的柜台,不同收入、年龄、职业、学历的人尽情的表演着自己的角色,随意的在场内选择.没有营业员不耐烦的眼光和别人的眼色。这种新的消费场所和消费环境使得城市人的购物消费形成了定向:买菜不再首选农贸市场而是进社区超市和大卖场;日常购物不再是街角的小卖部.而是商场里的大超市。这个具有“一次购足、就近便利、自主性选择强”特征的新的消费环境被赋予了“以人为本”、“自由、便利、平等”的符号意义,成为人们所认同的地方。
像网吧、酒吧、迪吧、r、,等新兴消费场所,是年轻人和中产阶层充分放松自我,展示自我,获得精神上满足的“理想地”。这类场所也被赋予着“时尚”“青春”“高品味”“主流”等符号意义。
另外还有像KFC一样的洋快餐店和咖啡厅,人们已经把它当作是悠闲消遣的好去处,在美国以快捷廉价取胜的快餐店到了中国却被赋予了不同的符号意义。洋快餐厅成了中国人们就餐的地方.人们很少关注快餐店食品本身,而是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似乎光顾肯德基、麦当劳可以体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文化”和“麦当劳”。他们“快捷”的特征也被“慢”所替代,其就餐时间往往长于美国。因为在肯德基店里舒适宜人的环境使得不少中国人将之作为闲聊、会友、新朋团聚、举行个人或家庭庆典仪式甚至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上述新兴消费方式、场所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西化的趋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国际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不光接受了西方全球化模式的话语方式.而且遵循西方的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西方的消费观念、方式也无不渗透到我们的消费市场,消费日益差异化、多元化、西方化。消费所承载的意义也日益丰富.消费的符号化也就日益凸现出来。新兴的消费场所所赋予的新的符号意义。使得人们昔日的消费观正在发生变化。而新兴消费场所的出现也使得人们不再是简单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而是更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和品质化。
(三)身份的符号意义
身份,是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每一个个人都是基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而存在的。正如我们在寻找自我的时候,必须将自我置于组织当中才能进行自我认识和定位;否则,任何一个以个人而存在的非社会成员,都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社会系统,从远古的氏族部落社会到现代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法制国家。这一系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对于生活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人,其社会关系的组成体现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联系,例如老师与学生、商人与消费者、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一样.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一论断来看.马克思否认了以人的肉身来决定个人的身份所属,而将它归咎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身份符号绝对是人的这“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突出代表。
一般来说,人的身份表现是多维度多形式的.服饰、首饰、语言、交通工具、居住环境等等一系列物品都能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身份。汉唐盛世中,人们推崇的多为一种大气、粗犷的精神.能够体现身份的东西也多为此类.如人们多喜胡服、骑射。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汗血宝马”。明清时.人们玉器的制作及玩赏达到一个顶峰.优质的玉器也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中国的古籍中把昆仑山称为”群玉之山”或”万山之祖”。《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因此,一件好的可随身而带的玉器,更是在不经意问凸现出主人的身份地位。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先富起来了。名车,豪宅,甚至是斗十千的金樽清酒让人眼花缭乱.而这样的花花世界也的确让人欲罢不能。就如电视里的广告:“x x x,是身份的象征。”便是这个时代消费理念的典型代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符号消费在我国社会中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大众传媒功不可没。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如今的广告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介绍、传递媒介。而是“通过营造与商品有关无关的生活方式印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品味的追求”。尽管人们有着选择消费的自由.但是往往还是收到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告也暗示着人们.传递着这样一种符号意义:不同款式、不同价格的物品应由不同职业、不同人群所使用。富有个性的广告语,以明星为代言人的广告等等不仅传播了特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激发人们追求消费品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符号意义所象征的生活方式的冲动。大众传媒总是无休止的追求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也对符号消费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物品的符号意义和空间的符号意义毫无疑问能够凸显出一个人的品味、内涵乃至是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钱了,便应进驻高档社区,购置豪华座驾,以名牌武装自己.出人高级娱乐场所。物品的符号意义和空间的符号意义都被我们进行着充分的挖掘。如今,我们采用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证明我们自身于他人不同所在。以此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所属。
三、小结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当中.一套完善而严密的礼制系统行使着给每个人赋予其应有的角色符号的作用。同时社会活动中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系统。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剧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次根本性的变迁。因此符号消费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凸现出来并非偶然,这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以发展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不是消费物,而是消费符号”这样的消费文化,日益渗透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并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符号消费.不仅影响了人们在需求内容和满足需求方式上的变化.而且人们的生活目的、生活愿望、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这种变化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不仅是消费文化的变化,也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整体性的文化的变化。
篇(7)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日本及新独立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挤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成就斐然,在制度建设上亦具有特色。当然,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路绝非平坦,在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挑战,有时候甚至是遭遇挫折。从 20 世纪90 年初开始,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失去的二十年弥漫日本社会;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相继袭击新加坡、韩国,虽然受打击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迫使两国进行调整。笔者以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不但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而且也是检阅与丰富制度建设理论的机会。
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研究国家转型时提出了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型国家、发展型国家、自主型国家和工具型国家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形态,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的。具体来说,国家形态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 治理结构) ,以及由此政治形态而产生的政治过程和治理绩效。〔1〕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典型的发展型国家。〔2〕根据查默斯约翰逊对日本经验的总结,发展型国家的构成要素有: 第一,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大、薪金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其职责是识别和选择需要发展的产业( 产业结构政策) 、促使选定产业迅速发展的最佳方案( 产业合理化政策) 、在指定的战略部门中监督竞争以确保在经济上的正常运行和效率。第二,具有一种官僚队伍拥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即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得超越保险阀的功能。第三,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国家必须注意保持竞争,但竞争的程度不超过经济优先的目标。第四,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3〕阿图尔科利从三个维度概括了发展型国家: 第一,在国家结构的变迁上,具有清晰变迁议程的中央权威的建立; 权威的非人格化; 经由纪律严明的官僚的建立,国家权威自上而下的渗透到社会之中。第二,国家首次建立了许多经济机构,而且提高了国家指导经济的能力。第三,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 在农村和城市,国家与有产阶级建立了联盟,一方面,国家欲求并成功地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增长,有产集团得到了足以保证持续盈利的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采取成功的压制劳工的策略控制农民和工人。〔4〕
结合约翰逊和科利等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发展型国家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出现,是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重大转型。一是治理权威的确立。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存在树立以发展导向的中央权威问题。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国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要解决的是更新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了这一任务。对韩国和新加坡而言,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或者最高国家权威,改变过去国家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变迁等问题上无所作为,或能力低下的状态,使国家拥有调控社会势力、将自己的意志渗透进社会之中的能力。二是在治理体制上,限制、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作用,突出行政机关在发展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设立新的经济机构,作为国家落实经济发展议程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建立纪律严明的、精干的官僚队伍,保证其不受党派政治的左右,使其能够根据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提出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 国家与城乡有产集团结盟,国家支持有产集团发展经济的活动,有产集团则对国家压制工人和农民的行为予以支持。三是在治理的内容上,国家将发展经济视为第一目标、第一任务,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发展经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