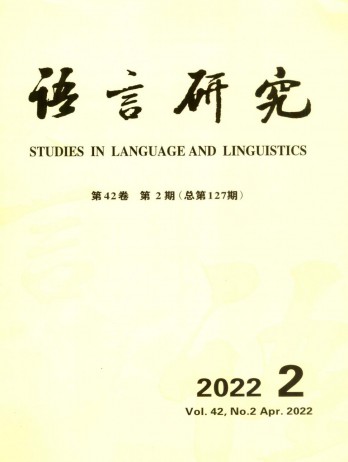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精品(七篇)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1)
关键词:延续性;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Stern.VonWright.NormanMalcolm.PeterHacker.Gorden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R.Shields、MarieMcGinnandBrainMcGinness以及Tim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of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offairs)、诸事况(the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8〕〔10〕雷梅英.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之宗教启示探究[D].2013.
〔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rans.D.F.PearsandB.B.McGuinness.TheTaylor&Francise-Library,2002.3.
〔7〕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23.
〔9〕徐有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6.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认知;语境论;语义论
一、语言哲学与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从哲学方面看,认知语言学来源于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它强调体验在认识世界中的积极作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和概念都可以从欧美20实际语言哲学中找到源头。例如,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就来源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由于前期和后期的重大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影响。《逻辑哲学论》是他早期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而后期的哲学思想则以《哲学研究》为代表。从维氏对语言哲学的影响上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则是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其精髓主要体现在他著名的语言游戏理论当中。从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点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学习语言学的人来说,了解语言哲学是一门必修的课程,也许踏着他们曾经的思想印迹,能让你在这些先哲的哲学思想里对语言的问题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和思索。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观以“语言图像”理论为代表,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坚持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语言关以“语言游戏”理论为代表,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也对认知语言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的语言能力依附于人的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哲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语言哲学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
1、语境论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19世纪到20世纪的下半叶当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语言的研究也出现了转向,语言学者们已将语言研究的视角从语言的内部转移到了语言的外部,从理想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的研究,从纯语言意义的研究转向了语言意义理解的研究。无论是格赖斯会话含义的理论,还是海尔姆斯的交际民族志学;无论是跨文化交际学,还是交际语言学,学者们都可以搜集到的日常语言为研究语料,并着重研究语言外部各个因素对语义理解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维特根斯坦曾试图借助于自然科学语言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语言。但是到了后期,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转变。他深刻地意识到,对活生生的语言的把握,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才能理解其丰富的含义。
从4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在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关注日常生活的语言哲学观点,对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斯汀和塞尔等。尤其是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奥斯汀的语言三分法,丰富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内容。而在这其中,他主要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影响。总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分为两大部分,而后期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对现代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是它们共同的特点。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领域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哲学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流派的产生,甚至在许多新兴语言学流派的理论中都能发现他的思想印记。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分析,有助于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理论,更能启发我们去深思和探索语言的本质。因为上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同时也催化了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而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必能促进和加深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逻辑原子论的奠基人,20实际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影响深远,并且和认知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两种思想都与语境有关,语境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一时期他的哲学理论的核心是图式说。在他这一时期的理论中,图式作为重点被创造出来的关键在于,图式在与它所对应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点的,这种共同点和一致性就是一致语境。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是着重实际看中使用的过程,这样对认知学科中主观意识的解释起重要作用。他主要从物理实在方面来解释,加强对人自身的研究,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从逻辑进行的,还从心理角度进行探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境观对认知哲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其从对知识逻辑语言的单纯研究中解放出来,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将知识同环境、心灵、现实存在相结合而进行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对情绪认知影响巨大,使我们知道认知主体要同外界发生交互关系时,必然在一定的情境下亲自涉身感受,这样就强调了环境对知觉的重要性。在认知研究过程中,情境认知和涉身认知是两个主要方面,从表面上看,情境认知是一种以环境为基础的认知,涉身认知是针对人自身的认知,这两种需要相互融合,在环境和事实的基础上,加强对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唯我的世界,而是一个与他人互动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从他后期哲学观点的巨大转变中可以看出,只有将自己融入现实真实的世界中,从能够向真理和确定的知识迈进,否则只会多走弯路,不会有所进步的。
2、语义论
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以来,语言意义的问题成了哲学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意义理论已经替代认识论成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乔治・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语科学的角度发展了意义理论。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发展了一样理论。米勒将语言问题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强调语言意义的作用。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所以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米勒尤其重视对词的意义研究,认为理解词义为理解更大单元的语义现象奠定了基础,是理解语义现象最重要的一部分。米勒在意义问题上持心理内在学说,坚持语言意义的心理内在立场,认为意义是心理建构的结构,而且意义的组织方式也呈现出心理结构特征。认知语义学在哲学领域也显示了特定的优越性。首先,认知语义学更有利于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体现了语义学研究的自然化趋向。其次,认知语义学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对言语者双方主体性的坚持,这样可以通过语义分析的过程将“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主体”进行有效整合,把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与言语者的心理自然性有效的结合。米勒认为对认知的研究之所以要包括对语言的研究是因为语言不仅是言语使用者的表现,而且还是一种能力,“对心智最好的研究就是研究其言语系统”。因此,这种语义学可以更加确切地合理地反映意义知识的形成与产生,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语义学的新进展。
认知语义学以心理实体来标定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心理性的。语义是从语言表达到认知结构的映射。语言本身是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所在的一个实体。认知语义学所强调的重点是词汇的意义而不是句子的意义。一个语言符号不是一个事物和一个名称之间的联结,而是一个观念和一个声音模式之间的联结。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原则有:1、意义是存在于认知模式(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实条件)中的概念。2、认知模式主要是由直觉决定的(意义并不独立于知觉)。3、语义成分以空间或拓扑客体为基础(不是可以根据某些规则系统而组成的符号)。4、认知模式主要是形象-图式性的。形象-图式通过隐喻和转喻方式而转换。5、语义学基本上是服务于句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由句法决定,句法不能被独立于语义学而描写。最后一个是语义的概念体现原型效应,认知语义学是以概念空间这一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认知的观点,语义学是语言和某一认知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
三、总结
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西方哲学的语言研究为认知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的独立及其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于认知语言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的发展与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继续为之努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商务印书馆,1996.
[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
[4]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元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
[5]萨皮尔.语言论[M].商务出版社,1985.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3)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4)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LinguisticPrisonCell:
AClarificationfortheFundamentalTraditionofWestPhilosophy
Keywords:Westphilosophy,Beings,thoughts,language,home
Abstract:ThewholehistoryofWestphilosophycouldbesummedupassuchastandardsyllogismofrelationinference:becausethoughtsisBeings’home(ancientphilosophy)andlanguageisthoughts’home(modernphilosophy),solanguageisBeings’home(thepresentphilosophy).NowthepuzzleofWestphilosophyiswhatlanguage’shome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著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5)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4]
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的出发点。”(8)[5]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6](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7]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潮流。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8]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9];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10]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11]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棗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著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第309节。
: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张振玉译. 坡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林语堂. 圣哲的智慧 [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冯智强.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强. 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 [J]. 三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6]王慧. 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创作 [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8]高桂英.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及其矛盾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篇(7)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1.进化认识论思想。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一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怎样作出贡献的?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是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要探究语言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必须探究语言是怎样以及为何被使用的,与人类社会和生命的进化有何相似之处。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经历自然选择和适应两个过程。选择是手段,适应是目的和结果。“顺应”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顺应指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是生物体为了生存而对自然选择范式作出的反应。在进化认识论中,这种观点被扩展至人类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用于解释人类的学习、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增长。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问题求解,其目的是增长科学知识,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正是这种顺应的结果之一。维索尔伦在考察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即选择与适应的思想。认为语言使用中选择时的趋优(利)心理与自然选择的存优去劣是极其相似的。既然在语言使用中选择普遍存在,顺应也自然具有普遍性。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