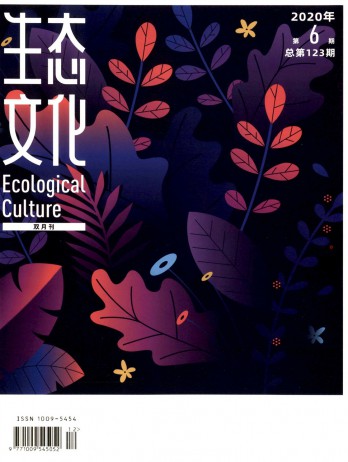文化研究精品(七篇)
时间:2022-11-10 18:44:31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研究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图分类号]I01;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154-05
从留声机、电话到有声电影、收录机、电视、随身听、家庭影院、多媒体电脑、手机、mp3多媒体播放器,20世纪的众多文化技术产物都与听觉密切相关;它们也不断重塑着我们的听觉习惯和文化经验。听觉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是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针对听觉感知及听觉艺术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文化研究者大多还没有像对视觉文化那样,对此予以足够的表述。近年来,国外人文社科界对“聋子”式的文化研究发出质疑,开始了继“视觉转向”之后的又一次“听觉转向”。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曾举办主题为“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转向,并不是要让“耳朵”来发难“眼睛”的话语地位,而是要借听觉话语来反思“读图时代”所衍生的视觉话语泡沫,从而达成对感官文化的整体均衡思考。
大约十年前,视觉文化研究响起了“雷声”,随后见到了见仁见智的“雨点”。听觉文化研究目前在国内既谈不上“雷声”,也谈不上“雨点”。当务之急,是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研究,并展开本土研究实践,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本土表述话语。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和科际整合的性质。目前,听觉文化研究需要整合各个话语领域,围绕两个关键问题来展开话语建设。其一是对声音本体和意义的追问,生发出关于声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社会、人文意义,和如何被生产、再生产、流通、想象、传输、消费等一系列问题。其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解读声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用作参考?研究模式如何?这两个问题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大致三个话语整合的方向,分别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相关。
一、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
音乐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听觉艺术形式,自然应该是听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探讨包括音乐但比音乐更加广阔的听觉现象。它与那些以“音乐”冠名的学科如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最大的不同,是十分重视动态的社会历史关系和听觉科技进展对听觉艺术形态变迁所起的关键作用。为了说明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研究特别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价值,有必要先对音乐诸学科和听觉文化这两种话语建构进行梳理。
首先需要梳理二者的知识谱系。音乐学是针对音乐的全面系统研究。它原本以研究西方音乐为主轴,现今已扩展到考察世界各地的音乐和相关问题,并走向多学科交叉,开始运用音乐理论、历史、音响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等多种知识话语。20世纪中期衍生的民族音乐学,进一步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带人了对具体民族音乐现象的研究,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如何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可以说,音乐学科研究话语的日益多元化,显示出与更大范围的听觉文化研究实现整合的可能。但也必须看到,音乐学界对听觉的思考仍然离不开艺术层面,离不开以西方古典、先锋音乐为参照来求解音乐艺术的普遍性及民族音乐的特殊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主要是在话语上涵盖之,将音乐艺术作为听觉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来对待,并从音乐以外的文化角度来配合解答音乐学话语所回答不了的音乐文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某些学者如身兼音乐家和学者双重背景的雷蒙德・默里・谢弗超越了音乐学、音乐史和音乐哲学的学科框架,在研究范式上将声音的“风景”(soundscape)纳入听觉文化的思考范围。在欧洲,法国学者阿塔里也较早从音乐专业以外的角度来解读音乐,其《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即在既有的音乐曲式、风格、流派话语框框之外讲述音乐随政治经济变迁的故事。
其次,从我国本土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不管是先前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还是后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及晚近的中国“音乐人类学”,有关狭义听觉艺术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音乐学、音乐史学科体系里。而另一方面,国内的都市和流行文化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音乐问题,却因为是音乐的“外行”而找不到有效的听觉表述话语,也没有意识到听觉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所以往往借用文化研究的一般话语来进行印象式、思潮式的评论。相比之下,目前海外学者已经开始从听觉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都市文化的发展进行研究。例如美国汉学家安德鲁・琼斯运用听觉文化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上海留声机文化,“”时期样板戏,大陆、台湾摇滚文化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囊括了对百年前和当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并对物质技术和知识话语的历史变革予以关注。比如现代出版业和唱片、有声电影业传人中国后,对中国音乐形态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体现在音乐教材和中国的戏曲、说唱、民间音乐得到了大量的出版和录制发行。这就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及实践本来就是西学东渐社会历史文化之下的产物,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演进绝不仅仅是音乐的内部事务。唯有将音乐学研究和听觉文化研究整合起来,才能全面地说清音乐和听觉文化发展的规律。
已故的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曾说:“我们对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如在艺术与科学的接壤之处,前来研究音乐听觉问题,恐怕就更将暴露出其间有关知识的贫弱了。”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接壤”,不仅意味着音乐艺术研究与听觉、媒体、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整合,也是音乐艺术研究与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的整合。这样,才能够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纵深里来求解关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
二、听觉文化研究:对文化史的整合
听觉文化史,简单地讲,就是从听觉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变迁。古代的人们通过演奏、吟咏、歌唱等手段来营造听觉共同体。尽管听觉手段和观念到现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人类文化栖居的方式总要包括听觉形态。那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不仅是个“观”的所在,里面也弥漫着听觉,“风月宝鉴”也是一面有声的魔镜。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一书从听觉分析人手来还原文化史,给通常是“无声”的文化史研究添加了难得的“音轨”。
这种研究日常感官生活变迁的方法属于“新文化史”,也在听觉文化研究里得到青睐。
除了科尔班以外,近年来在西方也出现了一批针对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听觉文化史研究成果。理查德,库仑,托斯通过对北美殖民地早期声音记录的剖析,发现了清教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地听觉的支配作用。卡林・比吉斯特威德研究了关于都市噪音的历史,展示了现代都市的阶级差距与声响环境差异的关系。另外有些学者则着重关注听觉感官的现代化问题,他们指出现代化不仅是科技、社会、理念的现代化,也是人类感官及其表征方式的现代化。艾米莉・汤普森描述了20世纪早期出现的“现代声音”技术产品是如何由现代社会意识所决定的。此前的现代性及其表征研究,总是在视觉观看、凝视、透视、图像技术里打转儿,无形中将现代性等同于“视觉现代性”。汤普森的听觉研究为关于现代性及其表征的文化研究打开了“听觉现代性”的维度。汤普森发现美国的声音景观在1900年到1933年问发生了剧烈的现代化转型。此过程开始于建筑声学,实现于声音与电磁波讯号转换技术的成熟。相应地,其《现代性的声音风景:美国1900-1933年的建筑声学及听觉文化》一书的叙事脉络就从世界上首个应用现代声学原理而建造的音乐厅――1900年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的落成讲起,结束于1932年底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落成。从音乐厅到办公楼,从声学实验室到电影公司的音效问,清晰、直接和无混响的理想的人造声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费。乔纳森・斯特恩把技术史看作人类感官变迁的投射,因为声音技术变革的前提是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变革。他在《可听见的过去:声音复制的文化源头》一书里谈到,电话的发明与听觉生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听觉生理学亦深陷于医学解剖学的错综文化史里。再如,早期留声机应用的重要动机是为了保存死者生前的声音或是保存消失的群体如印地安部落的声音。这与当时医学、标本学上的防腐技术革新是出于同样的文化动机,即资本主义在高速地走向未来的同时,想保存和展览“历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产阶级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私有化”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乡间。窗帘、玻璃窗、家庭书橱、照片簿、室内的煤气灯乃至电灯、留声机,营造了私人的感官空间,将公共感官生活抵挡在私宅之外。回荡在乡镇上空的钟声,曾经是西方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但他们的现代后人需要的却是私人的听觉空间不受钟声侵扰。私人听觉空间对公共听觉空间的胜利,不仅牵涉到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还牵涉到视觉和听觉的断裂。雷蒙德-默里・谢弗抓住了玻璃“眼见为实”但“视而不见”的用途,指出光滑透明的玻璃平面将整体的感官环境空间切为窗子里的听觉环境和窗子外的视觉环境。在现代的都市化阶段,当玻璃早已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而成为工业社会的必需品后,听觉经验进入了“室内装潢”阶段。鲍德里亚就称玻璃为“模范材质”,因为玻璃以“最高度的方式”体现了“气氛”的“根本暧昧”:“既亲近又遥远”。透过窗户看到的外部图像与室内的声音完全脱节,就如同同样的电影图像可以配上不同的音轨。这样的私有化模式的现代感知状态是经由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才成形的。
19世纪末到如今的声音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现代听觉经验与以往“断裂”。1876年,人类见证了第一次的电话交谈。两年后,爱迪生的电磁录音技术发明使得个体的声音可以超越有限的寿命而不朽。1899年,马科尼的无线电技术使人的声音得以跨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电磁波声讯技术提供了从天空到海底的广阔用武之地。到1930年,以美国声学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声学已经从建筑声学步入了电磁声学时代;麦克风、扩音器、广播、有线广播、有声电影等提供的电磁声音讯号也成为了重要的声音产品。后来又出现的电影音轨技术,是电磁声学的得力实验场和集大成者。影片里面的声音空间如同其视觉空间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虚拟”的。就连的“实况’’音乐演出也不再是“实际状况”了。各种乐器之间的音量平衡,可以通过运用多个麦克风和在操控台上进行的混合调节来实现“优化”。1932年底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无线电城音乐厅的开张,是对现代声音风景的礼赞,也标志着机器时代对声音进行控制的新高峰。
试想把19世纪欧洲乡村的钟声还原到当代,人们不会体察出其微妙且重要的文化意义。我们当代人的听觉感知,与科尔班书中所描述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了。马克思曾经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来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尽管原话有其十分具体的语境和意图,但他对物质性历史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现代历史不是孕育于“时代精神”的空中楼阁中,而是人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写就,经由感知经验进入社会意识。科尔班和汤普森等人的研究,即从听觉的侧面,从现代化转型到后现代转型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中强调了这一点。
三、听觉文化研究:对传媒学的整合
在现当代媒介中,声音媒介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极其复杂。20世纪初期的文化研究先驱本雅明就已从听觉技术和听觉感知角度,对现代文化的轨迹做了表述和预言。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技术复制问题不是视觉文化所独有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里对于唱片、留声机的留意。加拿大当代媒体理论家巴里・楚拉克斯说,当磁带录音机在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北美使用时,经常被叫做“声音镜子”。他说:“这面镜子,会在其表征中给现实加上主观‘色彩’且会框住现实。”当更现代的数字声音工具出现后,能让人更方便地对声音进行框取、切割、混合和分层。数字化的音乐传播方式已经把听者转化为听觉艺术家,具备了声音再表意的听觉“PS”能力。电脑的媒体编辑软件如iMovie和Windows MovieMaker、FinalCut Pro能满足声音文件的编辑需要,并且实现了文字、图像、声音的三位一体。
阿多诺在分析现代文化工业时,对听觉复制带来的认同感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在人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的收听,制造出了虚拟的“我们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是对直接进入人群的媒体干预式的模拟,无论身边是否有真实的人群和声音“原件”。在电磁声音复制转换、扩放技术之下,我们已经被电磁波转换后的复制声音所包围。在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的笔下,声音的机械复制造成了“声音分裂”(schizophonia),即“在声音的源头和其电磁波声学复制之间的分裂”。模仿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关于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会与其原有的“灵韵”分离的笔调,谢弗写道:“原初的声音是与发声的机制连在一起的。声音电磁波复制的声音变成了副本;它们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和空间里被重新播放。”㈣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来消费其声音副本。“声音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传播学意义上的社区空间。社区,传统上被联想为紧密联系的人群,现在延伸到辽远的互相不认识也没有接触的人之间,他们只是由于特定的听觉技术媒介才被联系到一起。阿多诺所描绘的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所营造的虚拟的“我们感”式和“相互陪伴下的孤
独”,进一步发展成为移动声讯时代个人空间的流动性和碎片化。孤独状态下的当代个体习惯于通过现代媒介来满足自足全知和相互依存两种心态的并存。那种“陪伴下的孤独”状态成为当下越来越多人的惬意的栖居的常态。这样的状态不仅局限于静止的室内,也经常是流动性的。汽车音响、手机、iPod等陪伴人们在流动的空间里穿行。麦克尔・布尔在对声音媒体文化中的个体行为的研究中指出,人们假装置身于喧嚣之外,让“音轨”与画面重新拼装,从而将环境审美化为“电影”式体验。于是,他们获得对环境的自主感和孤独中的“陪伴感”。他们自己订制的声音风景被“放置在两个耳朵之间”,重新组合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多样性。
篇(2)
【关键词】文化研究综述;翻译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69-01
在严肃、辩证的思维活动中,既没有“绝对的开始”又没有不间断的连续。不论是在思想史中备受宠爱、延续不断的“传统”,还是一度受到阿尔都塞学派热捧、强调认识中“对”与“错”的“认识论断裂说”,都不会存在这种情况。而我们发现凌乱、典型不平衡的发展起到了作用。具有价值的是,意义重大的断裂:思维的传统被打破、旧事物被替换、新旧元素在一套有别于从前的理论与基础之上重组。在复杂问题群中的变动完全改变了所提出问题的本质,所设置的形式,问题可答性的程度。此类观点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内在脑力劳动的成果,还反映了真实历史的演变;受个人思维控制的改造而无法提供思想以“正确性”的保证,取而代之以基本的方向、存在的状态的方式。个人思维与历史现实错综地连贯并反映在社会思潮中,以及知识与权力永恒的辩证,正因如此,这些断裂值得铭记。
篇(3)
唐杭州大慈寰中禪師考略
楊筠松生平、師承關係及著述考
敦煌寫本《大智度論》殘卷綴合研究
韓國東海三和寺水陸齋調研報告
瀕危的羌族口頭遺產和圖像經典
餽贈與象徵:論敦煌講唱文學中的禮物
敦煌本《觀音經》註釋的“雅俗”風格與淵源
《南嶽十八高僧傳》考
應縣木塔秘藏中的遼代卜筮書刻本
道教冥界組織與雷法信仰系統之關係
中國廁神女性性別成因及其內涵探究
劍川石窟文獻與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佛教信仰
韓國當代童話《五歲庵》中的觀音信仰
《大般若經字抄》與漢字研究
大足石刻文獻俗字考探
理解與誤讀:禪宗文獻在俄羅
“燕行录”中的各类中国民俗
滑稽镜像——传统独脚戏曲目中的民俗表现
从明清文献攷察火把节的来历
明皇驻跸白家村(川北民歌)
筆記小說對民俗語言的探求
況周頤筆記中的民俗史料舉隅
雲南楚雄古彝文《唐王書》題材來源新論
“曹山五位圖”圖像疑議辨證
清代時調對白蛇傳故事之接受——以馬頭調為主
恩愛與邪:中印文化視域中鴛鴦意象的不同建構
西王母信仰的道教化演變
近代民間的“保福”習俗
從藥師贊文考察藥師信仰與中華孝道之關係
古代僧傳中年齡稱謂詞匯釋——以三部《高僧傳》為中心
論郭巨埋兒的大鼓書和古今爭議
合生的發展及其表演之探究
契嵩《輔教編》中的因果報應與修證
海印三昧——《華嚴經》海洋符號解讀
民族、宗教与政治之汇通:试论西夏的大黑天信仰
从“地羊鬼”看华夏边缘的崑仑狗国神话
中国人的妖鬼信仰:以明传奇《剪灯新话》为视角
長崎、神户、京都地區華僑之普度勝會的傳承與當下
文化多樣性的人權宗旨——兼談俗文化的實踐研究原則
張繼《剡縣法臺寺灌頂壇詩》之解讀
羲和與麻姑故事所隱喻之時間觀及其文學敘寫
唐代白話詩中的地獄世界——以王梵志、寒山、拾得、龐居士詩為中心
不一樣的孟姜女故事——《銷釋孟姜忠烈貞節賢良寶卷》解讀
明清公案小說判詞與明清實際訴訟判詞的差異
從民間故事看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
淺議俗語言與漢語新詞新語——以《三國志》為例
淺論觀音信仰與儒家“孝”之結合——以孝女故事《沈清傳》爲中心
篇(4)
关键词:翻译 文化研究
翻译是随着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其主要任务是把一种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民族文化中。因此,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读者去接受异域文化,尽力实现文化再现,也就是再现源语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由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它也不会在真空中被接受,它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联,因此翻译研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生了文化转向,这首先得益于文化研究的兴起。
一 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出现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文学研究领域,起初只作为文学批评工具。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英国大学和成人教育领域的学者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如richard higgart的《读写的运用》和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在《文化与社会》中,williams指出,世界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完全了解它,因此也就没有哪种观点是有绝对优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不是旧的梦想中那个简单的重于一切的社会,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不断地调整和重新描绘,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天赋,要想参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太过繁杂。williams把文化看作是一群不断变化的符号,而不是单个实体。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宣告成立的历史性大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james holmes、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andre lefevere和英国学者沃克大学教授susan bassnett。该学派沿用了近代翻译研究中的阐释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在翻译研究学派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翻译领域的许多学者却常常困惑于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1990年,由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书中他们第一次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该学派近年来十分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具体实践,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她回顾了文化研究学派和翻译研究学派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程后指出,现在是这两种研究走向结合的时候了,文化研究能惠及翻译研究中对解码和编码过程的研究,因此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应该学习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拓展自己的研究疆域。
二 中国翻译学者的文化探讨
中国的翻译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努力找寻与西方同行共同感兴趣的切入点进行理论探讨,“……当前的文化研究可以作为切入点,打破跨文化交际和学术对话仅限于语言领域的桎梏。”(王宁,郭建中,2000:26)对此,王佐良先生早在1984年就撰写了《翻译与文化繁荣》及《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开创了文化和翻译研究的先河。王佐良先生指出,翻译涉及到语言和文化,译者应该既了解本国文化又要了解外国文化,而且还应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对比,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对等应该是意义、作用、范围和情感色彩的对等。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先生则指出,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将会取得巨大成就,从而导致翻译文化学(cultranslatology)的诞生。许崇信在其《文化交流与翻译》一文中倡导“”的翻译原则,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是怎样促进文化交流的,并且说明翻译的目的和特点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孙致礼认为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移植,因此译者需熟悉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
除了上述宏观的理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上对文化和翻译进行了探讨。郭建中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一文中论述了两种翻译策略——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策略和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策略。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以上两种策略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郭建中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归化”与“异化”之争。左飙在《文化的可译性》一文中提出,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可译性,文化的共性及文化融和使文化因素的翻译成为可能。
当前,翻译被看作是跨文化交际活动,这是由christiane nord在1991年提出的。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把一种语言中的文化内涵转换到另一语言中去,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译者对两种语言及其文化的差异的把握程度。王宁把翻译研究置于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指出翻译文学其实就是翻译文化,并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概念:
“…translation studies at least contains these two types of studies:in its narrow sense,dealing with literal translation aiming at turning the content i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language,and in its broad sense,exploring in turn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cultural form.the former is calle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the latter cultural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至少包括两方面:狭义上它研究的是字面翻译,即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广义上它研究如何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涵转而用另一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前者称为字面翻译,后者叫做文化翻译。)
从中可以看出,文化翻译强调的是如何把原文文化内涵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来,以及如何从译文文化角度来表现它。王宁在《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会拓展传统的翻译研究,使之从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转向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
三 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有了对话的平台——文化翻译。那么,文化和翻译到底有何种关系,文化研究为何对翻译研究会有如此之重要性呢?这就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
1 关于文化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词 “cultus”,意思是“发展”、“开化”。现在,文化的蕴涵极为丰富,由于视角不同,各国学者对其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以英国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最有权威性:“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他的定义侧重于精神内涵,后人对其进行了修正,补充了“实物”文化——文化是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总之,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全部成果。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通过自身的创造活动形成了文化,另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中又受到文化的熏陶,其举止行为受到了该文化的约束。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文化,同时又更新原有文化。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现着不同的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差异。
2 语言、文化和翻译
翻译必定涉及到语言,在弄清文化和翻译的关系之前必须先弄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紧密。人类的语言系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交际系统,除了生物和物理特征外,最主要的是它作为一种载体,传递了其他动物交际系统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文化。语言被视为人类表达自我的基本工具,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体现,是文化的载体,即一定区域内国家、民族和人群在生态、地域、物质文化、社会宗教直至语言文字本身诸方面独特而客观的描述方式与现实反映。没有语言,文化也就不可能存在和传承。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从前,人们认为妇女愚昧无知、地位低下,因此汉语中就有“男子汉不同妇女一般见识”、“妇人之见”等等表达方式。许多汉语贬义字都有“女”字偏旁,如:“奸”、“嫉”、“媚”、“婪”等。这些汉字反映了汉文化对妇女的歧视。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程度上,语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生活和思维方式。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及文化对语汇意义的影响十分广泛,如果不考虑其文化背景,任何语篇几乎都是难以充分理解的。例如,“他结婚了,太太是个母老虎。”如果不加解释地直译作:“he was married and had a tigress at home.”英语读者很难甚至根本不会理解tigress(母老虎)在该句中的文化内涵,因为在英语中会说:“he was married and had a lioness at home.”可见,在语言活动中,处处都有文化的烙印,时时可见文化的踪迹。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靠它来推进。语言是传承和交流文化的工具,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意味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涉及到文化的转换。历史表明,翻译源于文化交流,其主要目的是介绍异域文化。中国翻译史上的历次翻译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每一次的翻译都向中国引入了大量的异域文化,给古老的中华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例如,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影响,通过佛经的翻译在汉语中有充分的体现。佛教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我们日常使用的许多词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文化。佛教不仅给汉语带来了诸如金刚、阎罗、塔等等外来词汇,它还给汉语添加了许多常用俗语,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汉语成语是汉语词汇中的精华,其中有500多条与佛教有关。可见,翻译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能使文化充满活力。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更是文化的,它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建立“语言文化观”,不仅要力求翻译在语言意义上的等值,更重要的是要力求文化意义的等值。
四 小结
正如奈达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语言是文化的语言,词汇的意义深受其文化的影响,如果不仔细考虑其文化背景,就不能透彻地理解语篇。因此,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活动来说,双文化比双语更重要,因为词汇只在其文化中才有意义。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引导目的语读者感知源语文化。对于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捕捉到源语文化内涵并能在译作中表现出来。因此,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文化移入到另一种文化当中,从而使读者了解其它国家和其它民族的文化。
参考文献:
[1] bassnett,susan & 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nida,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篇(5)
【关键词】华山 审美 文化
从中西文化及审美趣味比较,从中华文化、民族心理、性格与精神的形成看,华山具有独特审美价值。西方是海洋与,中国是山水。中国的文化是山水文化,山水塑造了中华文化。如果说,日本的国山是富士山,中国的国山就是华山。
华山之美
巍巍华山以其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审美特性,陡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惊呆了人们。华山之美,在于自然美、精神美、人工美、自由美、体验美,也在于历史美、文化美。
自然美。华山以“奇拔峻秀”,驰名海内外。大自然如此钟秀于华人,赐如此之仙境。华山,气候湿润,一路景色迷人,云山雾海,宛若在仙界;雄险而不拒绝人们,博爱,接纳人们,人们络绎不绝。泰山可以封禅,而华山凶险而只能在山下西岳庙中象征性地祭拜,因而,也是自然景观保存比较完好的名山。
精神美。在传统文化及国人眼中,山水蕴含着宇宙无限奥妙,是得道、生慧,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和修身养性之处,是吸取天地精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处所。攀登华山,若入仙乡神府、顿觉心旷神怡,超然物外,万种俗念,一扫而空。华山之道,将人们引向天际天堂,是灵魂的升华与洗礼,是自我超越。是一个全新的自我,给每一位登临者以王者风范。壮我胸怀,壮我气魄,造就了英雄的中华儿女。
人工美。华山之险美,也在于“奇险天下第一山”、“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望而兴叹的登天石级之美。在峭壁绝崖上凿出的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等,以及凌空架设的长空栈道,三面临空的鹞子翻身,惊厥天下。登华山,惊心动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而尤其惊心于古人开辟天地的雄心与艰辛。
自由美。华山,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休闲方式和休闲理念。人本是自然,本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原初、最直接、最亲密、最深刻的关系,它让人感到自己存在于世界之中,让人亲切,让重新获得自由自在的自己,“诗意地栖居着”。爬行于山林之中,也利于清心寡欲、修身养性。
体验美。华山以其峻峭吸引了无数游览者。奇险能激发人的勇气和智慧,不畏险阻攀登的精神,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祖国山川的壮美。华山以雄伟、奇险、峻秀、挺拔著称于世, 若非亲临其境,不知其美。万丈深渊,峭壁嶙峋,山水意境令人留连。这种美,需要在登临的过程中,亲自并且反复体验。
历史美。华山位居中国中部,高峻华美,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承载,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山。华山的天然资质和人们登临华山的感受,孕育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千百年来,皇帝在这里祭祀,道士在这里修行,善男信女在这里烧香许愿,名人雅客在这里赋诗作画,给华山留下了众多的人文遗迹。中华民族的厚重、高傲、大气磅礴、阳刚、中庸、厚德载物、忍辱负重、坚毅、仁爱、博大、巍然屹立、堂堂正正、盛气、大义凛然等,不就是华山的形象吗?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华山,一览无余。
文化美。中国人基本上不必有向外求信仰、求拯救的需求。既然天是自然的天,那么“神道设教”的神道是神吗?不,“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依然是人,是人的灵魂与祖先崇拜,是教化之教、纲常礼教而非宗教之教。虽然中国人具有对祖先和天地的祭祀之礼,但这样的祭祀与其说是,莫如说是纪念追悼的礼仪。华山的祭拜,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
华山审美文化研究
渭南师范学院有司马迁研究,现在应该增加和开展华山文化研究,建议渭南市与渭南师范学院举办首届华山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目前为止华山研究明显不足。山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尤其华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缺乏研究。由华山审美研究开始,开拓到华山与中华文化研究,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促进和加强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引起同仁的注意和重视。作为渭南师范学院的教师,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国家与地方文化的研究工作。华山美学研究,抛砖引玉,引起陕西省乃至全国重视,组建华山文化研究会,促进华山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为渭南、陕西经济文化的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而对于登游华山者,大多是盲目的。不了解华山的审美意象、文化内涵,漠视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只停留于爬山,实际是对华山文化的忽视、贬低与巨大遗憾。人们大多也把华山这一名山当作一般的山,只是爬爬登登看看而已,这实在愧对华山。我们要运用美学,研究和揭示华山所包含的内在的审美意象,回归华山的审美意蕴,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对华山与其他四岳对比研究,挖掘华山之美,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华山之美。由此引申,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尤其华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需要厘清。提升华山的文化品味,注重华山的文化建设,提高华山审美品味。升华华山的旅游档次。扩大华山的审美宣传,吸引更多文化人士游览华山,提升华山的国际旅游档次。早在1992年华山开始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一阵热之后,从1999年,旅游体制改革,华山行政管理一分为三,条块交叉、矛盾交织,开始很久的“申遗”工作几乎陷入停顿,至今仍被拒于“世界遗产”门外,严重影响了华山应有的世界知名度和国际旅游档次。加强华山审美文化研究,形成文化热点,打破这一僵局,重启华山“申遗”工作,促进华山早日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参考文献:
[1]张崇文,张蕻.华山形态审美散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6.
[2]张勇,李祖坤.华山申报世界文化双遗产当快行[J].中国林业产业,2004,8.
篇(6)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文化符号 象征 实践
一、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弊端
文化符号是在集体中形成的,反映的是集体权威:符号作为社会共识,由于对个人意识的整合而产生了集体对个人的权威;而集体对个人的权威则通过符号传播和继承下去。符号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记号问题,而是“嵌在语言中的思维模式”(阿萨德,2008)。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体系,并在相互之间产生并不对等的影响。这些符号体系塑造并适应着相对应的生活,因而研究这些符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在符号的范畴之内进行研究却会带来许多麻烦。
第一个麻烦在于因符号的迥异而将不同阶层的文化截然分开,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文化符号代替文化,并将目光局限在某一种文化之中。以此方式进行研究的人往往自认为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要优于其他,因为他们实质上都认为文化符号高于文化,于是只要能从文化事象中抽取出文化符号,他们就胜利了。如果是从文化出发找到文化符号、再回到文化,还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研究路径;而从文化符号出发来研究文化符号就等而下之了,因为这是在一个业已形成且非常值得怀疑的框架之中来研究问题的――这就是顺次而来的第二个麻烦。
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在的生存框架(赵越胜,2011),尽管它看起来、也常常被认为是深深扎根于文化中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但由于符号代表的是一种集体权威而并非个人体验,因此“必须让陌生变为熟稔,与此同时又保留它的陌生性”(克拉潘扎诺,2008),这不仅仅是人类学者的悖论,也是每一个研究文化的人所要面临的分裂感。一旦使用了符号,便不得不服从于集体所共享的伦理、规范、制度和思潮,但这是否就是使用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尚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处于某种文化符号当中的人会被这些符号形塑,而被文化符号而不是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是缺乏内在平衡力的,他们经常感到自己的经历并不属于自己;而建立在此之上的研究也将无法平衡理论与现实。
二、去象以尽意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不受文化符号的限制之下进行文化研究?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人文传统,但问题在于,我们首先对于高雅文化符号更多地是进行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成为了高雅文化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民俗符号也不能保证对这些符号意义的准确理解,包含在其中的心路历程我们并不知晓。我们体会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符号带来的象征感,这些象征感就是激发起来的一种情绪,至于这些情绪确切的激发者是什么,却不尽相同。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同,尽管不如文化符号那样系统完善,却都是人类的情怀或精神。如果一味地用文化符号来理解文化,势必是对生活在文化中的人的不尊重,是一种经验对多种经验的专制,因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实践体悟被忽视了,而这恰恰是文化得以建立的根基。
文化不是用符号建立起来的,符号也并不胜过文化。说到底,人和文化本是一体,却被文化符号给隔开了,而且人身上的符号特性越来越多,文化特性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两种困境:
一种是预示论的倾向。预示论是对科学思想或学术思想早期各种各样表述的全力的、有目的的探寻(默顿,2006)。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中通过符号暗示的东西几乎是无穷的,此种观点视中国古代思想为一切思想之源泉,仿佛任何东西都是“古已有之”的,这使得研究者无法真正领会新思想和西方思想的意蕴,也无法真正明白自身的优点和不足。
另一种是希望古人的思想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无法解决便视这些思想为糟粕。中国式的学问固然能带给人许多启示,但无法给出答案。任何无视古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思想精髓,而希望将那些具体的方案加以推行的想法都是难以成功的。将现实问题和过去的思想混淆起来只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也浪费了古人的智力资源。
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研究之所以会依附于西方学术体系,或是陷入中国自己的符号体系之中却还认为这是“文化自觉”,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去除掩盖在精神实质之上的文化符号,而代之以实践体悟才能找到出路:思想和文化是建立在实践体悟的基础上的,文化符号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可以通过它来认识文化,但它永远都不能代替文化本身,代替不了在文化中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阿萨德.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谢元媛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克拉潘扎诺.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杨春宇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篇(7)
制度属于文化范畴。就制度文明而言,协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协商文化发展标志性成果,也是制度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协商制度形式及其内容。就今天我国协商民主发展与实践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无疑是人类协商文明史上新的里程碑,即协商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形下,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其实质就是协商治国理政,协商民主就是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愈益发挥重要作用。杨吉成的《中华协商文化刍论》一书,立意深远,俯仰古今,见微知著,广博厚重,给人以沧桑的历史感和厚重的文化感。著作以繁荣中华协商制度文明为统领,以突出文化“化成天下”为旨归,以强调协商的人文、和谐、同一等属性为枢要,重点介绍了协商文化及其协商民主的主要内涵、主要特征以及时代精神等,富有真知灼见,体现出广阔的研究视野和鲜明的研究特色。
一、创新性。
敢为人先,善之善者。理论的魅力在于创新及其对指导实践的普遍适用。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在于学理创新,在于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包括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作新的揭示、分析、预见及解答,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升华。本书的创新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空间宽度。当下协商文化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协商即协商民主角度着手遂行,而著者则是原创性研究广义协商文化,并坚持从民间、国家(王朝)、世界视野着眼研究广义协商文化,观点独立独到,诚可谓奠基式开先。二是时间长度。著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般的联想,以史家笔法,追根溯源,梳理脉络,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如通过“脉络轨迹”专章,举要劳动起源、协和处众、询谋则用、盟会朝会、采风制度、游说论政、星光阑珊、清议清谈诸章节,把千年百代的协商文化融入自家话语中,写出了中华协商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三是实践广度。著者遵循理论来源于实践圭臬,于2013年6月定稿并送审批立项,其专章论述“协商民主”,对协商民主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概括非常准确:民间参政新手段、宗旨意识新发展、新变化、社会建设新内涵、基层民主新发展,体现了协商民主之广泛性、多层性、人民性以及实践性特质。这与于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主题精神相吻合。
二、人文性。
万物之灵,惟人为大。“协者服也”,作者强调协商是为了人的事业。通过对协商文化概念的深入挖掘,表明:协,是一种事情、事业、事功、功业,甚至伟业。而这种事业,是靠众人之力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心甘情愿方能成就,是在和悦和谐的情状下进行。首先着眼于人,就是人文精神。著者定义协商概念包括包容性、平等性、民主性,强调协商首先是为了人。这尤为宝贵。
三、可读性。
诗化语言,诗之营构。对章节安排,可见著者煞费苦心,形式整齐,文字简约。既明白如话,而又思想涵蕴。比如著者说文化史,有“印迹昭昭焕史册,前贤后昆论短长”诗句比况。而第三章第七节“星光阑珊”中,“春秋战国,社会转型,诸侯争霸,征战频仍,乐坏礼崩,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或‘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却又商略开新,策士捭阖,谋士纵横,谋夫说客,各为其主,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协商文化一时好不盛兴”。语言颇为精当,饶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