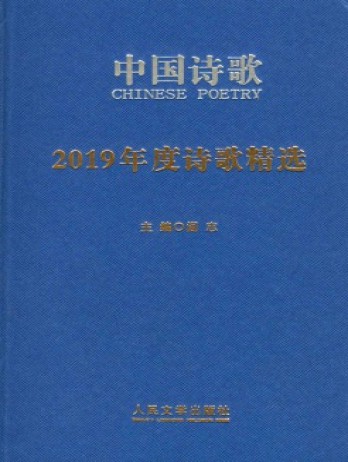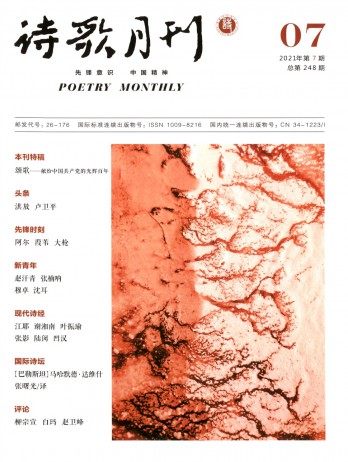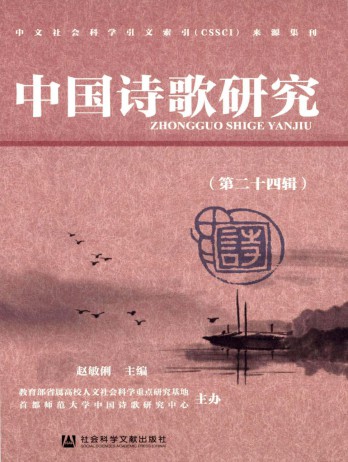诗歌的基本特征精品(七篇)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荻原朔太郎;意象;内部韵律;象征主义;日本近现代诗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53-03
荻原朔太郎(1886-1942),生于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著有《吠月》《青猫》《冰岛》等多部诗集、小说《猫町》以及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诗的原理》。其诗歌脱出时代局限,创作意识与手法颠覆了日本传统诗歌创作思想和审美方式,打破了当时新诗创作中和歌“姿”意蕴残留的局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其诗歌从文本到内涵、意象可以与西方同时期诗歌比肩,在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感、对自然的隔绝意识、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的最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北原白秋曾在为《吠月》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其为异常神经与情感的所有者,犹如饱含忧郁香水的剃刀。有多首诗歌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在日本家喻户晓,传诵度极高。可见,荻原的诗歌世界具有变幻莫测的多重魅力。
《吠月》作为荻原朔太郎的处女诗集发表于大正6年(1917年),也是其第一部象征诗集,共收录诗歌56首,是一部追求诗的纯粹性,执着于自己固有情感和感觉,充满想象力与紧张感的自由口语体诗集。诗人将语言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内在音乐性传达思想与情感。它的问世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官能的神经的战栗”“近代的孤独”“富于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可以说建立了日本近现代诗歌不灭的金字塔。明治40年到大正初年是日本“近代诗”的分水岭,标志着现代口语诗歌的确立。诗人菅谷矩雄曾说:“蒲原有明、岩野泡鸣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为何屡遭挫折。而朔太郎的《吠月》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近代诗向现代诗过渡的突破口。”[1]《吠月》的文学价值及在日本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本文试以朔太郎的首部象征诗集《吠月》为中心,探讨诗人在意象、内部韵律及象征主义诗艺3个方面的诗学主张,并分析《吠月》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动机。
一、意象说
“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通过意象可以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学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中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活、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2]《吠月》收录的诗作中的意象多为自然意象,包括植物类与动物类意象。如“竹”“菊”“猫”“犬”“贝”等,也有爱情类与抒怀类意象。这些看似老套陈旧的意象载体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森林里,被赋予新的生命,喻意和意韵也与古典和歌、汉诗相去甚远。正是这些陈旧却崭新的意象造就了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之大成。
其中,《竹》及《竹和它的哀伤》象征诗组最负盛名。“竹”是荻原朔太郎诗歌创作生涯中跨度最长的主题,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多次被日本高中国语教材所选用。诗作中的“竹”将荻原朔太郎的心理表象化,“竹”诗群通过“竹”这一植物意象诉说生命的某种疼痛。对自然的感受、理解力与感受方式是明治时期诗歌意识中尚未发现的,具有超前性。
竹子长在发光地面/长成一棵青竹/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
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严寒更显威武/竹子长在蓝天下/长吧 竹啊竹(罗兴典译)
“竹”意象属于植物类意象,《吠月》又属于抒情诗歌集,此类诗歌属于意象抒情诗。“竹”意象在众多植物意象中被荻原朔太郎所钟爱和反复书写,其承载的抒情功能隐藏在此意象之后。诗人借“竹”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病态的神经战栗和感觉上的剧烈疼痛。诗人在诗中诉说的正是内心深处的痛苦、悲哀与近似战栗的神经劳作。因此,“竹”对作者来说象征着生命,让读者感知到一种非日常的竹子的形象,“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根尖的纤毛象征着敏感纤细的神经,宛如诗人的神经像纤毛般鲜活可感,传递出来自生命内部最直接的情绪与感觉。荻原诗歌作品中呈现的疼痛的病理特质,与其疯狂的颠倒的、超越性的挣扎,是一种超越了近代的视角,其诗歌比之后的绝大多数的现代诗人的诗歌都要生动,更具现代性。
诗歌通过地上与地下两个视角,营造截然不同的意境。地面上,“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地面下“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展现了诗人思想上截然相反的两极,一端通过“锐不可阻”“拔节猛长”象征着心中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如同“竹节”仿佛可以无限生长,直达天际。借竹的生长态势诉说其精神的向往与需求。而地面以下却是在无边黑暗中战栗着的,如同竹子根须般敏感纤细而又焦躁不安的神经,努力向光明伸出手臂,却又时常落入失望的深渊。
日本森林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对植物怀有亲切感的国家,“竹”也被诗人从古书写、吟诵至今,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收录了咏竹诗多达30多首,而其多承载着“闲寂幽雅”古典审美旨趣。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世界里,“竹”是一种神秘的意象。诗人将对人、世界的关系障碍与疏离感,通过染上生理上畸形色彩的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以丰富多彩的象征手法传达而出。“竹”深深植根于大地,外直中空,构成自我存在中心的空虚世界,其中却包纳了森罗万象之回响。诗人借竹节内部的“空”暗示自我精神世界与情绪的纷繁复杂。“空”中有情感的千种可能,万般涌动。在“竹”固有的“屹立于天地”的意象的基础上,诗人赋予了其病态、冰冷、幽森的意象。
变异性意象的生成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经过主观想象的变异,完成客观物象的改造,是主体化意象中的一种。可见,荻原朔太郎诗歌中的“竹”是一种在原有物象的基础上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变异性意象,成为诗人诉说“战栗的神经”“敏感”“焦躁”“不安”乃至“病态”的一种符号。诗人借意象化改变诗歌的思维与想象方式,用象征意象呈现暗示性,以多重性的意蕴空间,表现近代人的复杂生活与近代情绪,这在日本当时诗坛是一次较为深层的本体性的变革。
二、内部韵律论
受西方象征主义思潮影响,荻原朔太郎推崇内部韵律论(内在节奏论),即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诗歌是内心浪潮卷起的声波。诗人强调“双韵律论”,诗句的节奏与韵律,脱出诗歌本身无形的内心、情感的律动,是作为“内容的音乐”,不是形式上的音乐,而是感觉上的音乐。诗的韵律是指从人的内心深处涌动喷薄而至的内在旋律,是根本意义上的诗的动机。《吠月》时期朔太郎诗歌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于贯穿于文本的情感与感觉上的律动。
然而,诗人并未因对内部韵律的推崇而忽略诗歌本身的节奏与韵律。语言不能表达情绪的地方还有音乐和诗歌。“由音乐与美术所代表的这样显著的两极的对照,是普遍于一切艺术之中,而成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东西的对照。即是,主观的一切艺术,是类属于音乐的特色;而客观的一切,其本质上则属于美术的范畴。就文学说,诗与音乐相同,是高扬着热情的,温暖的主观”[3];从这一论断可知,诗人认为音乐与诗歌本质是相通的,诗歌这种“主观”类属于音乐之特色,由此可见其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而诗人又精通音律,擅长演奏曼陀林,对音乐的热爱,在诗歌上体现为对韵律的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说,音乐诉诸听觉,绘画诉诸视觉,而诗歌诉诸于语言,语言的文本形式和文字载体只有诉诸于声音时,才能在韵律上倍增曼妙。一言以蔽之,诗人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及诗歌“内部韵律”的推崇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吠月》及以后的诗集之中。
光る地面に竹が生え/青竹が生え/地下には竹の根が生え/根がしだいにほそらみ/根の先より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けぶる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ふるへ。
かたき地面に竹が生え/地上にするどく竹が生え/まっしぐらに竹が生え/訾欷牍りんりんと/青空のもとに竹が生え/竹、竹、竹が生え。(《竹》节选自《吠月》)
原诗在除第一、二两节第四句之外的每句韵脚均使用了“え”,即[e]音。(第一节尾句“へ”的发音与“え”相同)。诗中多处使用“生え”(意为生长)一词,意图用动词连用形的反复,营造出一种焦躁与不安的感觉。荻原朔太郎在多个诗作中使用“同语反复”的创作手法,通过反复来加强其音乐性与韵律感。在《吠月》序言中提到,“我内心的‘悲伤’‘喜悦’‘寂寞’‘恐惧’这些用其他语言及文章难以表达的复杂而特殊的感情,我通过自己诗歌的韵律来表达。可是韵律有时是难以进行说明的。韵律只有靠以心传心。能感知如此旋律的人才能与我促膝相谈”[4],可见诗人是“双韵律”论的提倡和完美执行者。
三、象征主义诗艺
荻原朔太郎在《诗的原理》第五章《象征》中提到:“诗精神之第一义感的东西,都是基调于此种宗教情操,所以若称此为象征,则一切诗的最高感,必定都是象征。”[5]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导精神,《吠月》之后的《青猫》等诗集都有浓郁的象征主义气息。
象征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与主张是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一方面要求诗歌有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另一方面要求表达诗人内在的“心灵的旋律”“灵魂的音乐”。荻原朔太郎的诗作在幻觉中构筑意象,具有极具暗示性的“神秘的内容”,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兴起于西方,在被各国接受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该国固有文化传统与文学土壤的影响。象征主义在诗歌领域的成就最高,诸多伟大的诗人皆为象征主义大师。自20世纪初西方象征主义传到日本,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对日本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荻原朔太郎的诗歌中明显可见对波德莱尔诗歌思想与象征理念的接受。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以幽暗、丑陋、病态”为美,建立的意象灰冷阴森,意境幽抑沉郁。在传入日本初期被以田山花袋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批评为“病态”“恶魔主义”“艺术至上主义”“颓废”,却丝毫不影响象征主义在日本文学、思想、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发展与渗透,影响直至今日。
《吠月》中收录的《危险的散步》《酒精中毒者之死》《青蛙之死》等诗作弥散着黑暗、阴冷、病态的气息,无不体现对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继承。关于朔太郎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沉醉,佐藤|洋O在《日本近代叙情诗事情》一文中指出:“我们即使不曾耳闻朔太郎在《新》中的直接告白,‘在鸦片吸食者的梦里,像波德莱尔样的人,总在苍白病魔的身影里梦游,在其反面的人格中隐藏着明澈如白昼般的理性,仅做想象既会痛心的现代的悲哀,我对波德莱怀有燃烧般的热爱。’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波德莱尔的倾慕无处不在。”[6]
由此可见,荻原朔太郎作为推崇波德莱尔的日本近现代诗歌代表诗人,深得象征主义神髓,将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等象征主义的几大要素完美地糅合于诗作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艺术成就是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
荻原朔太郎在诗歌意象的探索中,吸纳了象征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对古典审美意识的颠覆,古典传统美学中的幽暗意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贫相的精神障碍。
诗人主张诗歌表达的目的并非为了情调的情调,也非为了幻觉的幻觉,更不是为了某种思想而做的宣传演绎,而是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重视诗歌的“内部韵律”,认为诗歌的真正韵律来自文本内部,是情感与感觉的律动;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接受与发扬,建立了其独特的意象繁杂、光怪陆离的象征森林,给人因“视”“听”“感”多层次的想象与感受的空间。《吠月》收录的诗歌脱离了华言丽语的堆砌,唯美意境的营造,不书风华雪月,不赋强说之愁。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菅谷矩雄.诗的リズム音数律的イニする?蔟ト续编.东京:大和房,1978.35.
〔2〕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文学评论,2005,(3).
〔3〕〔5〕荻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09,291.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2)
一.怀古诗
怀古诗将史事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的遭遇(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或对历史作冷静理性的思考与评价(如杜牧《赤壁》)。
①形式标志:标题中常有古迹,古人名,或在其前加“咏”,或在其后加“怀古”、“咏怀”等。
②特征意象:古迹、古代建功立业的人物
③基本主题:a.寄托诗人追慕前贤、建功立业的志向;b.抒发昔盛今衰的感慨,暗含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多为借古讽(伤)今;c.揭露统治者的昏庸,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担忧国家、民族的命运;d.悲叹年华易逝,壮志未酬。
二.送别诗
1、形式标志:标题中一般有“别”、“赠”、“送”等字眼。
2、特征意象:柳、酒、歌、船(舟)、长亭、短亭、灞陵桥、南浦。
3、基本主题:①依依不舍的留恋;②离情别恨的愁绪;③对友人的思念;④从对方落笔,写友人念己,实则反映自己孤寂情怀。
三.羁旅行役诗、闺怨诗
古人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飘泊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他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内容上或触景生情(如中秋望月、重阳登高),或托物传情(如月、雁、笛、柳)。
1、特征意象:驿道、征铎、马、船、舟、杜鹃、鸿雁、客、浮萍、飞蓬。
2、羁旅诗的基本主题:行旅之人的旅途艰辛、飘泊无依、浪迹天涯、归期遥遥、孤独彷徨、清冷孤寂、思乡思亲。
3、闺怨诗的主题:①表现妇女对出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或对战争的厌恶;②表现宫中女子自由被禁锢,遭人冷落的怨恨以及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四.边塞诗
从先秦就有了战争,边塞为主题的诗歌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频仍,士子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要比科举进身容易的多,且统治者尚武轻文,再加上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斗的时代气氛,雄奇壮丽的边塞诗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边塞诗派。
1、形式标志:标题中含塞、征等字,有的用乐府旧题(如凉州词、从军行等)。
2、特征意象:玉门关、阳关、胡人、胡马、羌笛、明月、大漠、胡天等。
3、基本主题:①表现雄奇壮丽的边塞景观;②建功立业,奋勇杀敌、视死卫国的决心;③山河破碎的痛苦;④久居边关的思乡之愁;⑤塞外生活的艰辛苦痛;⑥报国无门的怨愤;⑦归家无望的哀痛。
五.山水田园诗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之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之先河,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张籍、王建。
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新洗练。这类诗歌的特点常常是情景交融。
1、特征意象:高山流水、明月清风、农家风光、山间盛景。
2、基本主题:①寄情田园山水,渴望安静、恬淡以及农家的悠闲与欢乐;②描绘山川美景,抒发热爱祖国山河之情;③厌弃官场黑暗,抒发闲适情调,表达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和隐逸情怀;④写作特点:借景抒情,融情于景。
六.咏物言志诗
1、形式标志:往往以“咏梅”“秋菊”“孤桐”等为题,常用比喻、拟人、象征等表现手法,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寄托某种志趣、精神、品格。
2、特征意象: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等。
3、主题内容:借所咏之物表达自己的心志或追求,或表达对生活的思考,或对人世的评价。
4、分析角度:抓住物与人的相同点,物我合一的结合点加以赏析。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象征主义;梁宗岱;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207-02
美国理论学家韦勒克说:“不仅在法国而且遍及西方世界,20世纪诗歌观念已为法国象征主义运动所宣明的学说原理一统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象征主义潮流传入五四时期的中国,给力求改变传统文学又对新的文学迷惘彷徨的青年作家们找到了一个别样的出路,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使象征主义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象征主义就其整体而言,确实受惠于欧洲象征主义的理论更多,而不是象征主义作品。因为在文学理论界都把梁宗岱被奉为中国象征主义的理论中坚,而且他也与法国象征主义大师瓦莱里有过密切交往,所以本文意在从理论层面上结合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观反观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下的诗学观的相似相通,从而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本土化找到更好的阐释。
梁宗岱认为象征有两个特征: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淌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这里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说是象征的艺术结构特征,是就“情”与“景”、“意”与“象”的“淌恍迷离,融成一片”的关系说的;这里的第二个特征可以说是象征的艺术效果特征,是就象征在意义上暗示的艺术效果而言。梁宗岱因此把艺术的象征称之为“赋形”,将象征蕴藏的丰富的艺术境界称为“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结合两者提出“象征的灵境”,这是他提出的关于新诗的最高境界,是他在融会贯通中西传统诗学而独创的一个诗学概念,是一个在特定中国文化语境中既注重内在蕴籍、又注重诗歌的形式表现的诗歌理论。一方面深的法国象征主义中“应和论”,诗歌语言的暗示行特征精髓,另一个方面又自然地融合了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情、景”、“意、象”和“意境”观念。
象征概念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把象征型艺术称为美学的开端。黑格尔定义:象征就是意义或感性存在与其暗示的意义的结合。这里的象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符号或标志,而具有暗示的理性的内容。正是暗示的存在,决定了象征的所指和意义,也决定了象征双关和歧义的本质。西方的二元世界观强调两个世界的存在:感性的世界和理性的超验的世界。作为象征主义开创者的波德莱尔深受二元论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天地万物相互应和的理论。在写作方法上,波德莱尔主张打破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艺术手段,希望有声有色的具体物象来暗示显现内心微妙的世界。而魏尔伦强调“运用音乐和暗示的方法,表达出情绪的起伏和内心的神秘”,兰波把诗的暗示性提升到更深的境界,他的《元音》诗发明了元音色彩,揭示了元音字母丰富的象征意义。
马拉美把暗示性诗歌主张推向一个极端的境地,使象征主义诗论趋于成熟,他说:“与直接表现对象相反,我认为必须去暗示。对于对象的观照,以及由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这种观照和形象就是歌……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一点一点滴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的状态”在答记者问中,他进一步阐释了暗示性诗歌理想: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种趣味原是要一点一点去领会它。暗示,才是我们的理想,一点一点滴去复活一件东西,通过一连串疑难的解答去揭示其中的精神状态,必须充分发挥构成象征的这种神秘作用。”马拉美的暗示说表达了一种更明确的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用审美观照的方式去把握对象,从而达到心与物的契合,并由此感悟诗的境界。用暗示、暗指无营造梦幻般的朦胧的象征意境,从而揭示心灵的奥秘、超越直观世界并达到对纯美的把握和表现。马拉美还提出:“诗歌应该永远是个迷”,要“叫人一点一点去猜想”,如他的诗歌《天鹅》便可看出其中的多义性、朦胧性和神秘性特征,这也是源于对象征主义的美学追求。
黑格尔断言:“象征主义是艺术的开始”,“主要源于东方”,象征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或是创作方法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中国象征主义又是怎么结合中西象征手法的呢?
周作人准确滴把握到“兴”与象征共同之处是将物与心境沟通,旨在营造诗歌蕴藏含蓄的意境,表现诗歌的“正意”、“精意”,是克服新诗直白的叙事说理弊端的有效艺术手段。周作人虽然没有对象征与“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但他的象征即“兴”说指出了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中国古典诗艺在审美本质上的相通性,并敏锐地意识到中西诗艺的“融化”将会开拓出中国新诗无限广阔的发展道路。
梁宗岱丰富和深化了周作人提出的“象征即兴”说,把象征的解说从单一的艺术手法引向了更深的理论层面。他说:“我以为它(指象征)和诗经中的‘兴’颇为相似”。他肯定了《文心雕龙》对“兴”的解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他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去理解《文心雕龙》对“兴”的解说并使其与象征会通:“所谓‘微’便是两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关,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象征底微妙,‘依微拟义’这几个字颇能道出”他指出象征与“兴”的奥妙之处都在于能表现出物与物、人与物内在的共感。中国古典诗歌的“兴”“以物起情”,情随物而动,以致“情与物冥”,诗情由物引出并融化于物象之中,又使物象化为意象,升华为一种灵境,此时景语即情语,情语也即景语;象征的妙处也在于能创造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正式因为两者都具有使“万物冥合”的审美功能,所以梁宗岱才能说象征与“兴”相通,也才能以“契合说”为核心,把象征这个西方的诗学观念植入中国诗学中来。梁宗岱提出的“象征的灵境”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意境”理论与王国维“境界”理论的发展主要在于:站在象征主义的诗学的立场,在强调“情”与“景”融洽无间的基础上,把“意境”理论引向了注重艺术形式的道路,也这是梁宗岱本人所理解的“赋形”与“灵境”的浑融的艺术境界。
虽然九叶派诗人最终完成了现代手法和古典诗歌传统的结合的“新诗现代化”,但是之前梁宗岱及其后的叶公超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反观和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这对九叶派的诗学视野的开阔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梁宗岱对中西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树,与鲁迅“拿来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他的诗学理论是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象征主义理论体系,他以象征为契机,以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为基础融合了中西方诗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为象征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建设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陈太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乐黛云.梁宗岱.穿越的象征主义[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3]梁宗岱.诗与真[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4)
论文摘要:费密,明清之际重要的学者和诗人。他的学术思想以儒为宗,诗歌创作理论上也秉承儒家中正平和的诗教观念,在博学众家的同时,追求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费密强调诗歌创作的法度,以为诗歌应“以深厚为本,以和缓为调,以善寄托为妙”。他的诗歌创作分别从诗歌的内容、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方面作出努力,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明末清初新繁(今属四川)人,曾组织武装对抗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以遗民身份流寓于扬州、泰州一带,布衣终身。费密在扬、泰期间交游广阔,所交往者多为当时名士,如钱谦益、屈大均、冒辟疆、王士稹、龚贤等,形式大多为以诗会友。所至之处,评价颇高,渐至于名动一方。其青年时期即被称之为“西南三子”之一,后<清国史馆儒林传》评之日“至今谈蜀诗者,推费氏为太宗”。…费密著作颇丰,《燕峰集》有诗二十卷之多,但大多散佚,现存《燕峰诗钞》有诗三百余首,艺术价值极高,在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人作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费密成名于蜀中,大半生生活于扬、泰之间,诗歌创作以宗唐为主,也受到扬、泰地域群体性诗风的影响,但费密诗歌并未拘泥于前人诗作或受时人诗歌风气左右,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诗歌认识与追求。费密的思想以儒学为宗,这一点也成为费密诗歌美学的基本出发点。费诗总体上秉承了中正平和的儒家诗教观念,从此出发,费密在诗歌创作上极为看重诗歌的法度,费密子费锡璜在《中文先生家传》中提到:“(费密)教诸门人及不肖诗文法最精严,不轻许可,故凡得闻考余风,诗文有法度”“……于八家则爱昌黎,故所为文浩然如水之无涯,而未尝骋才矜气也;为诗则以深厚为本,以和缓为调,以善寄托为妙,常戒雕巧快新之语,故浅于诗者即不能知考之诗矣。”此两段评价皆是其子品评费密之言,从中可以间接判断出费密对诗歌美学风貌的认识和追求:诗歌应遵循儒家诗教念,讲求法度,分而言之,则应以内容深厚为根本,从容和缓为表征,在此基础上再追求善兴寄之妙境。费密的诗歌创作佐证了这一点,从其诗歌作品角度来阐释其诗学追求,所谓深厚,是指诗歌内容要深重厚实,关注现实,不为虚言;所谓和缓,是指诗歌的气韵要舒展从容,不能急迫局促,大气而不促狭;所谓寄托,是指诗歌需要一定的艺术技巧,切忌浅白直露,而以比兴寄托为佳。作为儒学思想家,费密“不为矫异,不为苟同,广而不滥,博而有要,剿绝浮辞,引归大道,议人从恕,遇事持平。”其修身立命的思想在于保持中正平和的态度,戒绝骄躁之心,不以性情从事,仁和宽恕,不作妄言。这些思想外化到诗歌创作中,便使得费密诗歌有了谨严的法度和深厚、和缓、善兴寄的风格。
1深厚
费密诗歌所追求的“深厚”风格主要是指诗歌的内容而言。费密主张诗歌创作应该有充实的内容,杜绝虚假矫饰的情感与无病的内容。分而言之,也就是在诗歌创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内容上要“深”,不能只是流于表面形式,泛泛而谈,而应该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在诗歌创作所反映的情感内容上要“厚”,追求情真意切的效果,不能无病,故作矫情。具体而言,费密诗歌对内容的深厚的追求,反映在以下两点:
首先,任何文章都应是作者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政论和思想方面的著述中,费密感慨时人对明末蜀中张献忠之乱的不了解而妄加揣测,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述《荒书》来为历史正名;同样,在文学创作上,费密也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表达发自内心的思想态度。
费密“常谓锡琮、锡璜日:‘吾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218著述总是写自己所历、所见、所闻、所思,不作虚妄度测之言。诗歌作为文学艺术允许个人的想象、生发空间的存在,当然不必拘泥于“皆身经历而后笔之”,但也应该来自于自己真实的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触。费密在蜀乱期间,饱经沧桑,年少早熟,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如《北征》、《易裙行》等均取材于诗人实际生活,以主观视角去反映蜀乱惨况,现实主义风格强烈,可谓清初蜀乱史诗。费密出川后足迹所至一十四省,结交名士不可胜数,诗歌风格呈多样化发展,代表其主流诗风的感怀诗、田园诗风格也前后不尽统一,但这些诗歌都源自于诗人真实生活体验,毫无矫情之言。费锡璜在评价他父亲的创作时说道:“考与论经术及古文诗词,言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也”。这样的评论正印证了费密诗歌的特点,唯有务实,不为虚言,诗歌的主旨方得以深厚。
其次,费密诗歌的内容深厚,表现出费密有意识地追求丰富深厚的学识基础。费密认为,为诗应重学识:一方面应该博闻强记,遍习古书,打下深厚的学问基础;另一方面,要强调诗人丰富的识见,抛弃杂说,宗于儒术。有了深厚的学问与丰富的识见基础,诗歌方能免除轻浮溜滑之弊,自然表现出中正肃穆、味旨深远的特点。当然,深厚丰富的学问与个人识见并非旦夕之力所能够轻易达到,那需要诗人的循序渐进的勤苦学习,日积月累方能有所成就。费密在授徒诗法时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张子昭)甫事密焉,乃以文辞来请。数年子昭合户坟册,尽弃所为诗歌,依止于古,清婉秀洁篇章大殊矣。夫诗之为物,若灵花异果,味甘芳远,然时蓄之勤,非旦夕之力,晚节渐于诗律细往毓己。如此,子昭既决志古学,不为杂说所惑也。”费密强调深厚的学识基础,并非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去刻意显现自己学识的广博,或去卖弄奇字僻典,或故意去翻新出奇,这样只会导致诗歌佶屈聱牙的弊端,导致诗歌内容表达与情感抒发的结果大坏。反观费密的诗歌,大多具有平白晓畅之美,在诗歌中应用典故较少,生僻字更可说全无。费密提倡深厚丰富识见主要是为了避免诗歌轻滑浮躁之病,只要在为学时循序渐进,戒除浮躁,真正的具有深厚的学问与丰富的识见基础,久而久之,诗味自然醇厚。
2和缓
费密诗歌追求的“和缓”风貌主要是针对诗歌内涵的表现形式而言。费密主张诗歌气韵舒展和缓,不急迫局促;诗歌气格庄重典雅,大气而不促狭;语言文字朴素淡雅,戒除雕巧快新的弊端。费密对诗歌风格的和缓追求仍是从中正平和的儒学诗教观出发而产生的,从整体上创作风貌上来看,费密诗歌正表现出他所追求的“和缓”艺术特色。
首先,费诗和缓风貌表现为诗歌的气韵舒展,气脉贯通,流畅而从容不追。从费密的总体诗歌创作来看,他的诗歌风格乃是宗于唐诗的,尤其是初、盛唐诗歌。而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重“情”,情感的充沛使得盛唐诗歌往往气韵饱满,气势飞动,诗歌流畅而气脉贯通,从而在整体上显现出气韵饱满、流畅的风貌。费密的诗歌并不追求宋诗的理趣,宋诗好议论的特点必然会影响到诗歌气韵的流畅性,这也是费密诗歌宗唐的原因之一。当然,唐人诗歌情感上的抒发手段多种多样,费密在对唐人诗歌进行批评时,鲜明的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性,他对中、晚唐诗人与诗歌大多予以贬低,而对初、盛唐诗人大加推崇。其中,他所推崇的沈宋、王孟、李杜等人的诗歌各有特色,但大多气韵舒展,气脉贯通,气势流畅。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则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尤其是费密的感怀诗,非常重视诗歌的情感特征,丝毫不事议论和说教,情感浓郁强烈,气韵自然流畅。
其次,费诗气格追求庄重典雅,在整体上现出大方之气,免于流俗之弊。费密作为儒学思想家,处世庄重持平,在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上则追求“大气”,要求诗歌达到有气有格的境界。他在与友论诗时说道:“自沈、宋定近体诗,声韵铿锵,文采绚烂,有气有格,亦古亦今,固诗中之杰作,可以垂法后世者也。然繁音促节,错彩镂金,质淡消散,古瑟渐稀。时移风转,至于元白之轻俚、温李之织艳,长吉、卢仝之怪癖,下逮晚唐诸公之小近卑寒,风雅之道于斯变极,愈变愈恶矣”。从此可见,费密认为为诗歌应重气格,元白诗歌过于轻俚导致滑俗,温李的诗歌风过于格艳丽浮华陷于庸俗,李贺、卢仝的诗歌过于追求奇巧而导致怪癖,这些诗风都绝非正途,在气格上陷愈流俗之弊,不够庄重典雅,最终导致“小近卑寒”,诗歌气格卑小而毫无大方之气。费密所认为的“大气”标准并不单纯,在他看来,如“李峤之和平。王勃之精丽,沈宋之典重,王维之舍雅,孟浩然之自然,岑嘉州之疏秀,李白之高华,杜甫之悲壮”姗,这些诗歌气格方是“洵文章之能事也”。在费密诗歌中创作中,他对各种气格可以说都进行了一些尝试,但表现出的最强烈特征便是庄重典雅并时有悲壮。在诸种诗体中,律诗尤其是五言律诗最适合表现费密在诗歌气格方面的追求,因而反映在费密的诗歌创作中,五言律诗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
再次,与费密对诗歌气格的追求相适应,费密诗歌追求语言的凝练深厚、平白晓畅之美。一方面,费密饱经世乱,身兼爱国志士与儒者双重身份,身世经历与杜甫相类似,诗风受到杜甫影响很大。尤其表现在诗歌语言上,费诗非常重视遣词造句与文字的锤炼,诗歌语言大多精干有力,安排意象时空间、时间感强烈,往往达到峰峦层障、波澜迭起的艺术表现效果,气势雄健奇矫。以其代表作《过朝天峡》为例:
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
暮色偏悲客,风光易感人,明年在何处,妻子共沾巾。
诗歌并未采用新奇的语言,也没有使用典故,但语言凝练、厚重,而且语意连贯,中间没有丝毫停顿,诗语汩汩滔滔而来,一气呵成。诗歌中的“断”、“流”、“接”、“偏”、“易”等字的应用可谓千锤百炼,夺造化之功;另一方面,在对诗歌的功用上,费密遵循了“诗言志”的传统,只是将之作为抒发自己胸怀和情感的载体,而未将之作为载道的工具,诗歌里没有丝毫枯燥的说教。他的诗歌既不追求使用尖新、生僻的词语,也不轻易化用前人的旧作与使用典故,更没有卖弄文采、炫耀学问,诗歌的整体语言风貌显得平白晓畅,极为自然。
总之,费密诗歌的语言既不过于浅白,也不过于富丽繁华,更不奇巧怪癖,而是注重语言的锤炼,,凝练而不事雕琢,流畅而不事尖新,不用生僻词汇,不卖弄文采、炫耀才学,整体效果干净利落,其语峰所指,表意尽兴方止。这种凝练晓畅的语言与费密抑郁不平的感情配合起来,形成了费诗雄深雅健的特色。
3善寄托
费密虽然强调诗人学问的深厚,追求诗歌内容思想的真实与表现形式的和缓、庄重。但费密并不排斥诗歌中艺术性的表情达意的技巧和方法。缺少比兴寄托等手法,诗歌直白式的表达方式只会导致诗歌情感、内容的浅显乏味,在诗歌中表情达意应该“以善寄托为妙”——将诗人自己的情感融于景物、意象、人、事当中去,充分发挥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增强诗歌艺术效果。
费密诗歌追求“善寄托”的艺术效果在诗作中表现极为明显。费密的感怀诗大都是关于自己身世际遇的情感抒发,这样的情感由于费密的不幸人生际遇而起,自然属于本自于费密内心的真情实感。费密在抒发这样的情感时,并不直白,或移情于景,或借景抒情,如“大将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暮色偏悲客,风光易感人”中的景物利用:大江孤艇、残春暮色,这样的景物描绘出的阔大境界与作者的感伤情绪结合在一起,使得人生悲情显得更加辽阔久远,可谓是景情相生,水融。费密诗歌主体情感基调是清冷哀伤,但诗人漂泊多年,历尽沧桑,晚年安居田园生活自然会生出欣喜之情。作者在田园诗中抒发这样的感情时,也并不直白,如“日暮掩书徐出户,水边闲立看鸭飞”(《村中晚吟》),诗句中无片言只字提到诗人的情感,但择取的一个生活典型细节就足以表明作者对闲适乡居生活的惬意之情。
费密追求诗歌的“善寄托”也典型地反映在费诗对意象的运用上。费密作为遗民诗人,入清以后,国破家亡,为生计四处奔波,身世凄凉,多有亡国之恨与身世之悲,内心情感低沉悲怆。他的诗歌在表达这些情感内容时,善于使用兴寄手法,利用一系列的特定意象来表达情思。在费密诗歌意象体系中。“江”、“山”出现频率最高,成为费密诗歌中的核心意象。一方面,费密大半生浪荡江湖之中,无论是四川,还是扬州、泰州地区都紧临大江,所做诗歌与江水相关本是自然不过,但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江水作为意象与费密的心境有着契合之处:江水本身漂浮不定的特征与费密在江湖中乱世漂泊、沉浮不定的身世际遇可以相通;江水绵延不断,与费密王国离家的满腹愁情可以相通;江流浩荡,一望无涯,对应个人之渺小,易使人产生江湖之大,此身何寄之感,也与费密的心境契合。因此费密常借与江水相关的事物比兴,抒发自己亡国之恨与羁旅愁情,这样便以江水意象为核心,将舟船、芦苇、江月、山川、孤客、雾、霜等意象结合于一处形成一个小规模的抒情意象体系。另一方面,费密在出川时饱览蜀中山川,在流寓东南的过程中也遍访名山。
山具有艰险的特征,尤其是蜀山,难于上青天。费密在客旅中常借山川之艰险寄托人生旅途艰难之意,长诗《北征》便是代表。但在费密诗歌中,“山”意象的比兴意义不止于此。中国文人很早就有隐遁山林的传统,乱世隐遁尤其是文人普遍愿意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费密作为儒学思想者,修身齐家的思想让他抵触隐居修道之念,社会现实和繁重的家庭生计也不容许他这样做,但费密的内心世界却隐藏着渴望一份幽清安静的情怀,这种情怀正好和“山”意象富含的象征含义相通。配合大半生不幸的悲凉情绪,费密在诗歌中以“山”意象为基础,兼采云气、山鸟、山月、老树、苔藓、山雾、松风、雪、霜等意象,形成又一个意象体系,来寄托自己心灰意冷,渴望隐逸之意。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敦煌;写本;诗歌;读者传写;传播;编辑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3―0111―06
自公元105年蔡伦发明“蔡侯纸”后,中国人写字行文就开始使用这种方便易得的新材料,形成的文本称为抄本或写本。新媒介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抄本时代的文本传播遂大不同于此前的简牍时代,也不同于之后的雕版印刷时代(刻本时代)。在这方面,传世文献有诸多记载,更可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丰富的抄本实物可供参照――敦煌文献。5万余件敦煌写本,主要集中于9、10世纪,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抄本(写本)的鼎盛期。如果要探讨抄本时代文本的编辑、复制、流传等传播问题,敦煌写本无疑是一座宝库。本文即集中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现存的敦煌诗歌写本为四百多个,在敦煌文献中所占比例很小。敦煌学研究中,敦煌诗歌也不算热门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王国维、潘重规等对《秦妇吟》的考订与研究;王重民、潘重规、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对《全唐诗》的补编、校订工作;黄永武、徐俊等对敦煌诗歌的整理校辑;胡适、[法]戴密微、张锡厚、潘重规、朱凤玉、项楚等对王梵志诗歌的研究;王重民、潘重规、柴剑虹、陈国灿等对陷蕃诗的研究。总体来看,文字校订和内容解读方面的成果较突出。
要考察敦煌写本的传播特征,最好能见到实物。但除少数人外,现有条件很难达到。其次是基于二手资料,即已发表的敦煌写本照片、写本外在形态的研究等。目前,以《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为代表的写本照片资料已接近完善,嘉惠学林良多。但写本外在形态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日本、法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有一定帮助,但很零散。大陆学者则基本延续了王重民开始的以校勘、辑佚为主的文献学思路,侧重于为写本确定年代、作者、校勘文句,进一步延伸至内容解读。这些工作当然十分重要,但文献学思路基本来自藏书家的观点,即确定善本。因此,对于写本传播方面的信息,如卷子的大小、装帧、编辑特征、为何而制等,大都是忽略的。
最早注意到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特点的是徐俊和朱凤玉。徐俊在2000年谈到:“敦煌诗歌写本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遗物,……与刻本时代相比,写本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朱凤玉在2008年对百年敦煌诗歌的研究进行回顾时,也明确提出“敦煌诗歌的流传是以写本传播,此与一般雕版印刷的传世诗集不同。传世的唐人诗集大抵经过文士编辑、校阅,然后付诸刊印,其形式固定,文本统一。后世翻刻,虽有版本不一的情形,然文字歧异不大。敦煌诗歌以写本形式流传,形态多样,且为读者信手传抄,大抵未经编辑整饬,抄者鲜有编辑意识,因此不存在定本概念”。
两位学者均意识到了敦煌诗歌写本具有不同于刻本时代的传播特征,如“信手传抄”、“鲜有编辑意识”、“不存在定本概念”、“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等,但所述均较笼统,对其原因更未进行过深入分析。本文拟在徐、朱二位学者的基础上,结合王重民、藤枝晃、池田温、潘重规、荣新江等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照敦煌文献的图版照片,系统论述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并重点阐述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所依据的敦煌诗歌写本材料,主要基于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一、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至少要包含下述问题:唐代敦煌,人们如何获取和复制诗歌文本?这些文本是如何编集的?文字抄写、版式安排有何特征?
传播意味着要有复制。敦煌诗歌写本的复制方式为手抄。这种抄写复制行为,称为“传写”或“传抄”,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是汉唐时期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敦煌诗歌写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存在方式看,敦煌诗歌写本可分两类:诗集和单篇。其主体是诗集。单篇指一件写本只抄一首诗作,如《秦妇吟》,此类写本很少。诗集又包括别集(个人诗集)和集抄(集合数种诗作或数个诗人的选集)两种类型,以集抄为多。
从传播的角度看诗集,至少要知道它的名称、作者、编者、编选思想等信息。以此来看敦煌诗歌写本,立刻会发现,此类信息几近缺失。“既无书名又无编者,也无编例可寻的诗歌选本所占比例最大。……敦煌诗歌写本与传统意义上的‘诗集’概念存在着相当大差异”。这种现象的产生,部分可能与敦煌诗集写本均为残卷有关,但总体来看,即使将残卷因素考虑在内,依然会一头雾水。
1 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
先看诗集名称。现存敦煌写本,极少数残卷上保留有集名如“故陈子昂集”、“珠英集”、“王梵志诗集”等。绝大部分今人熟悉的《唐人选唐诗》、《高适诗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等敦煌写本集名,其实并非残卷上原有的题署,而是罗振玉、王重民等早期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们根据集子内容推测或拟定的名称,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集名已证明并不准确②。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多以“唐诗丛抄”“诗钞”等为名,一方面更符合敦煌写本原貌,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诗集的名称实在无从查考。
再看作者。在徐俊统计的63种诗集中,只有《伦人王克茂诗抄》、《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李矫杂咏注》、《李翔涉道诗》、《释玄本五台山圣境赞》、《高适诗集》、《张祜诗集》、《岑参诗集》、《赵嘏读史编年诗卷上》、《吴均诗集》等十数件,能确定作者身份(部分经后人考订而定名)。存写本30余件的《王梵志诗集》,虽然有的标明为王梵志,但潘重规、项楚早已指出,王梵志诗的作者并非王梵志,而是众多白话诗人作品的集合体。那些集抄类的诗集写本,其中的作者信息更是十分随意,有的诗作下面标明作者,有的则不标,所标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作者姓名,很可能是托名之作。五百多首零散诗作中,作者留有姓名且大致能考证出生平的,不到30位。
第三,编者情况。王梵志诗集的编者无从查考。其他敦煌诗集写本中,《玉台新咏》、《珠英集》的残卷上找不到编者信息,是后人据传世文献记载,断定其编者为徐陵和崔融。另有《瑶池新咏》(原残卷上无此题名,为后人考定),其残页上存有编者信息:“著作郎蔡省风纂。”除此而外,绝大部分敦煌诗集,均无法找到编者信息。
2 无明确的编集思想
但凡诗文集,一般都会在一定的编集思想下聚合作品。会有比较明确的编选标准;诗作编选也要按一定的顺序,如时间、题材等。在诗集的外在形式上,要有序言、目录、作者姓名、诗题等基本要素;每页的版面也有具体要求,让集子看上去整齐统一。
但遍观敦煌诗歌写本,完全找不到此类编集思想。
首先,找不到诗集的编选思路。多数诗集都是随意挑选作者与作品,随意排序。不同体裁的作品合抄不在少数:“就诗歌作品而言,与曲子词、宗教赞颂、辞赋以及变文等讲唱作品合钞的写本并不在少数”,“在收录诗人诗作的多寡上,也表现出较多的随意性,通常没有明确的起止”。偶有几部能够看出一些编选思路,如部分王梵志诗集写本,另外存诗155首的《心海集》:“从五、七言至道篇的分开排列,使我们隐约可见《心海集》各篇排列规则的存在。”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敦煌诗集,后人无从判断其编集思路。
其次,诗集的抄写形制随意。以被视作精品的两个写本为例。一是存诗三十余首的“唐诗词丛钞”残卷,此卷首尾俱残,抄于《古文尚书》残卷卷背。徐俊称此卷“行款严整,书法甚佳,为敦煌诗卷中的精品”。对照原卷图版,我们会发现,虽然此卷整体上还算齐整,但其抄写格式显然十分随意:首先,所有诗作均不署作者;其次,诗题有的单独占一行,有的则与首句同处一行;第三,如果诗题与首句同在一行,诗题与首句之间,有的仅空不足一字,有的则空出好几字;第四,“古贤集一卷秦王无道”一句连着抄了两遍。再如,徐俊视为敦煌诗卷精品之最的“唐诗丛抄”。此卷字体端正,格式齐整,长篇抄写而无涂改痕迹,说明抄写者十分认真,但大部分诗作不标作者;有的署作者名,有的则署作者官职;有的诗题单占一行;有的上首诗的末句与下首诗的诗题同行,很难找出其抄写规范。精品尚且如此,其他诗集抄写形制上的随意可想而知。
3 异文现象突出
读者传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错字、漏字、改字等异文现象。在敦煌诗歌写本中,此类现象十分突出。
同一首诗,如果出现在数个敦煌诗歌写本中,那么,诗题和诗作文字必然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异文。如《沙州墩煌二十泳并序》有六个写本,或题《敦煌古迹廿泳序》,或题《墩煌贰拾泳并序》,或题《敦煌廿》。与之相比,诗作文字的异文更为突出。李白的《惜蹲空》(即《将进酒》),在敦煌写本中,有三个集子收录,对照这三首诗,尽管整体框架不变,但几乎每一句都有异文(如以其中一首为底本,校以其他两本,异文表现为脱字、衍字和某字不同,偶有一句会完全不同)。再如《龙门赋》一首,在敦煌文献中共见有四个抄本。对照这四个抄本,几乎每句都有某个字不同,有的明显是笔误,如“侠客骄矜仙结伴”中将“侠”写为“使”。有些则难以判断,如“城中歌舞纷相乱”,或写为“纷然乱”。很显然,越是反复抄写的作品,异文现象就越多。《秦妇吟》、《古贤集》等,无不如此。
如果再与传世文献比较,那么,敦煌诗歌写本中的文字错讹现象更是不胜枚举,诗题异名、作者误属现象也十分普遍。
二、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特征的形成原因
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明显缺失;无明确的编集思路;抄写形制随意;异文丛生。是什么原因导致敦煌诗歌写本形成这样的传播特征呢?笔者以为,有三方面因素最为重要:1.自抄自用的读者传写模式;2.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3.敦煌的地域特征及敦煌文献的性质。
1 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
敦煌诗歌是在读者传写过程中形成的。读者传写的基本方式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供读者自己使用。“传写”的最终目的是供读者自己使用。敦煌诗歌写本编集随意、抄写随意、异文丛生,形成此类特征的原因首先就在于读者的“自抄自用”。徐俊发现,在敦煌诗歌写本中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改写现象”,有改动而又“若隐若现”,表明传写者基本能够维持原本的面貌,但毕竟是用于自己阅读,改动也很自然。
2 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
自抄自用带来了敦煌诗歌写本编集、抄写随意、异文丛生等特征。朱凤玉因此认为:敦煌诗歌写本不存在“定本”概念。但为何无定本概念?
就文本传播来讲,人们总希望得到一个作品完整而确定的文本――定本。这一观念早在西汉,已很明显,以刘向、刘歆为代表的大规模官方校书,是为起始。此后,自汉末至唐代的刻立石经、朝廷颁布典籍等行为,同样基于定本传播的观念。从历史实际情况看,这种定本观念主要集中于官方主流识形态领域,最主要的是经学,除此而外,佛、道教经典,史部类书等,也归属其中。在此类领域中,由于有定本观念,校勘、注释行为十分频繁,且抄写规范,质量精准。但在其他文字领域,如诗歌,定本观念就十分薄弱。这种定本观念的差异,在敦煌文献中体现得很明显。
敦煌文献包括佛教文献、儒家文献、道教文献、官私文书等,真正在敦煌当地大量传写的是佛经和儒家经籍(佛教文献约占90%)。此类典籍,一方面数量最多,另一方面,均有着严谨的校勘规范和抄写流程,其写本也大都有标准版式,如目录、序言、卷次、纸张大小等。
相比之下,那些非官方统一生产、非士人晋身必试文本、非官方推崇的书籍,在敦煌,其写本的传写格式就很随意,如诗歌、曲子词、变文等。这也是学界共识:“敦煌卷子中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很多是由名写生工楷书写,还经过一校再校的勘正,阅读起来困难较少。但是,俗文学如变文、曲子词等,多半是经俗手写俗字而流传下来的。”
理解唐代,或者说抄本时代“定本”观念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敦煌诗歌写本的编辑会处于无序状态。诗歌写本在整个敦煌文献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这种文献构成情况已经表明,9、10世纪(中唐至宋初)的敦煌地区,诗歌文本在当地的传写是很边缘化的。客观上,读者传写这种模式必然带来异文现象;主观上,唐人对诗歌定本的忽视,以及自抄自用的意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编选和抄写上的极大随意性。
3 敦煌地理位置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
尽管抄本传播中存在定本观念的差异,但如与同时代的传世文献相比,敦煌诗歌写本所体现出的定本观念又显得过于薄弱。从传世文献看,唐代诗集的编辑并不像敦煌写本那样。以唐人选唐诗为例,现存唐人选唐诗集子如元结《箧中集》、殷瑶《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等,均有明确的编集理念,选诗标准明晰,多用序言说明编选意图,编排均有一定之规。如《箧中集》所选多为抒发作者仕途无望、生活贫苦的诗歌;《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天宝时诗,选取的标准是“声律”、“风骨”兼备;《国秀集》选开元前后诗作,以诗人时代先后为序编排;《中兴间气集》选录肃宗、代宗时期的诗,以“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为标准。上述诗集,我们今天看到的虽然均为宋以后的刊印本,其具体的编辑体例很可能经过了宋以后人的改动。但至少在编选主旨上,上述选本均十分明确。与之相比,同样是唐人选唐诗,敦煌诗集的表现就完全不如人意。那么,该如何看待此种现象?笔者以为,需要充分考虑到敦煌地理位置以及敦煌文献的特殊性质。
敦煌在唐帝国统治下,有过约一百余年的繁荣稳定期(692―786),中间经历了开元、天宝盛世。在全国统一、国力蒸蒸日上的大环境下,敦煌也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帝制王国的一部分,敦煌的所有建制完全贯彻唐帝国的规定,文化同样如此,终唐一世,敦煌一直与帝国文化制度、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敦煌文献即清晰地体现出此特点,儒、佛、道等经典的内容与抄写规制,官学寺学中传授的知识文本,均与帝国保持一致,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也正是唐代整体文化传播观念的体现。因此,在文本传播上,敦煌大致可以看作是唐代抄本传播的一个缩影。
但是,敦煌依然有其特殊性。它毕竟远离唐帝国中心,在唐代中后期,由于吐蕃的占领,它几乎处于文化上的孤岛状态。归义军统治的近二百年中,社会稳定,重拾汉文化①,但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再如以前那样紧密,更多地处于自治状态,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也远不如前。另外,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教育及文化水平均远远落后于中原。佛教在敦煌很盛,敦煌文献中,佛典是最大宗,但其所藏还是远远比不上中原,“如果按《开元录》组织的唐五代寺院中完整规范的藏经来要求藏经洞藏品,当然就会认为它们是废弃物,但当年的三界寺藏经本来就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真伪混乱”。唐代是诗的王国,无论古体还是近体诗,均已达到了巅峰状态。然而今存敦煌写本中的诗歌,传抄自中原的大多不是精品,而是通俗易懂的作品;本地创作的诗歌,艺术水平普遍较低。这些均说明,当地的文化水平不高。儒佛道经典等有官方写本,规范清楚,照样抄写即可。但对诗歌,编集上本就无明确规范可资参照,偏远再加战乱,中原传来的诗歌抄本也不可能多,要选择好诗,考验的又是编选者的文学修养,考虑到敦煌当地文化水平的实际情况,其诗文编选及抄写上的粗陋也就在所难免。
另外,还要考虑到敦煌文献的特殊性。目前学界基本认同,藏经洞中的主体文献属于敦煌的一个小寺――三界寺。敦煌文献里的写本,在当时,都是一些常见文本,三界寺又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寺,也不可能存留什么重要精致的文献。读者传写中,本就不受重视的诗歌,其写本面貌的简陋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结语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诗性;诗性智慧;自我指涉;原始思维;互渗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性”一词在文学研究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尽管它在构词法上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无论是名词poeticity或形容词poetic),知识谱系也主要源于西方,却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汉语概念,为汉语学术界所喜爱。“诗性”、“诗性智慧”、“原始思维”、“互渗律”和“自我指涉”都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学者们往往各取所需,或者在其间游移不定。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其含义甚至会严重扭曲,遮蔽古代汉语文本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整理“诗性”概念的知识谱系,并对其用法进行反思。
一、诗的特性
诗性即诗的特性,这种说法虽有同义反复之嫌,但从字面上看是顺理成章的。由于诗歌的定义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诗的特性难以界定,诗与非诗之间的界限也不够清晰。而按照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看法,诗歌等体裁(文类)的划分其实是一种期待视野,是学者对诗歌文体的某种建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先看辞典中的“诗歌”条目:
诗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它简练地表达出富有想象力的体验,运用精心挑选、构筑起来的语言,通过意义、声音和节奏引起特殊的情感反应。大体而言,诗在大多数文化当中都被认为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形式,它起源于早期社会中的巫术符咒、仪式上的咒语和极富节奏感和高度形式化的讲述。{1}
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它借助于具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语言,构造具有诗美的意象,表现诗人强烈而凝练的情致。{2}
专业辞典一般都会指出诗歌的情感性、想象性、讲究节奏韵律等特点,而文学理论教材则更多地强调诗歌的形式特征。比如“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③,“运用比兴、象征、拟人、隐喻、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呈现出跳跃性结构”,“语言特别凝练,更讲究陌生化,具有节奏和韵律,富于音乐性”,“有特殊的诗法”。{1}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认为,格律和隐喻是诗歌的基本组织原则,要给诗歌下定义就必须包含这两个因素。韦勒克则从“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四个术语入手来研究诗歌的结构。这些解释勾勒出了诗歌的主要特征,代表了关于诗歌的通行看法。诸如此类的诗歌概念,是“诗性”概念的重要参照物。考德威尔将诗歌的特征概括为七个方面,即“诗是有节律的,不能翻译的,非理性的,非象征的,具体的,并有浓缩审美情感的特征”,以及诗由词语组成,而“词语引起的不仅是观念,它还有激发感情的‘光焰’”。他认为“这些特点足以使诗脱离文学的整体而独立”。{2}这一概括吸收了西方古典文论的观点,也受到新批评的影响,是对现代派文学实践的一个总结。
考虑到中西诗歌在文本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定义将更为困难。诗歌(乃至文学)在西方和中国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处于完全不同的论域,关于这一点,余虹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辨析。③如果按照英语诗歌(poetry)的标准来衡量汉语诗歌(诗),或者按照汉语诗歌的标准来衡量英语诗歌,恐怕得出的结论都会令人瞠目。如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那么,是否也有两种不同的诗性呢?
既然没有统一的“诗歌”定义,那么,关注“诗歌”一词的用法也许就够了:就语言形式而言,诗歌与散文相对;就想象性而言,诗歌与历史相对;就形象性而言,诗歌与哲学相对;就情感性而言,诗歌与科学相对。因此,诗性意味着某种与历史性、思辨性、科学性、逻辑性相对立的特征。情感性、想象性、节奏感,这三者的结合大体就可以造就一首“合格”的诗。而“诗性”一词的通常用法,也基本上以这三点为核心。
在汉语学术界,这个概念被频繁使用,跟“意境”、“境界”、“空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它隐含着一层意思:诗性意味着一个超出了具体可感的物质世界的“空间”,一个微妙、丰富的情感世界,乃至指向一个超凡脱俗的“超验”世界。考虑到超验世界在传统中的模糊和缺乏,“诗性”的暗示作用就更为重要了。
由于诗歌是一个多面体,而“情感”、“想象”、“节奏”三者并非在同一层面上界定诗歌,所以,如果将诗性等同于诗歌的特性,“诗性”的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确定,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甚至无法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或者清晰描述内在的分歧,从而无法真正推动讨论的深入。
二、诗性语言
如果无法从诗歌自动推导出“诗性”的定义,不妨换一个角度,将焦点对准“诗的语言”或“诗性语言”,看看西方文论关于诗性语言(诗歌语言)及文学语言(“诗”常常是文学的代名词)的论述。
关于诗性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差异,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论述最为著名。比如,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的语言在功能上最大限度地“突出”自身,而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虽然“突出”在标准语言尤其是在政论文章中十分普遍,但“在诗的语言中,突出到达了极强限度: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4}。巴赫金认为“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语言在这里不仅仅是交际手段和描写表达手段,它还是描写的对象”,作家应该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克服幼稚的语言和教条的语言,克服狭隘的单语体性和盲目的多语体性,也就是无风格性”。{5}而所谓无风格的语言,不仅是指工具性的语言,还包括那些程式化的文学语言。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日常语言)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形象和象征,而在于“其结构的感觉特点”。诗歌是一套程序(device,手法),其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现实,而是要创造一种幻象,扰乱那些习惯性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方式,因此“诗就是受阻的、变形的言语。诗歌言语是建构言语,而散文是普通言语:节约的、灵活的、合理的”{1}。诗歌通过发音、词汇、结构等方面的特殊的技巧使对象“陌生化”,故意以复杂的形式来增加感知的难度,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自身。他提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核心预设,即“文学文本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符号的组织。文本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突显或者揭示出自身的建构手段(也就是让它的建构性特征引人注目),通过陌生化策略使现实变得陌生”{2}。诗歌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幻象,陌生化(突出、反常化)程序是诗性语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瑞恰慈将语言的用法分为两种,一是以指称为核心的科学用法,一是以态度为核心的情感用法。③他所说的情感语言,就是诗性语言或文学性的语言。韦勒克认为,要给文学下定义,就必须弄清文学中语言的特殊用法,弄清文学语言、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主要区别。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和暗示性,强调对文字符号本身的注意,强调语词的声音象征,强调情感态度的表达,而科学语言趋向于使用类似数学符号的标志系统,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并且特别指出:
在某几国高度发展的文学中,特别是在某些时代中,诗人只须采用业已形成的诗歌语言体制就可以了,也可以说,那是已经诗化的语言。然而,每一种艺术作品都必须给予原有材料(包拾上述的语源)以某种秩序、组织或统一性。{4}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汉语诗歌中的情形,在《诗经》、楚辞、汉赋、骈文、格律诗及其相关原则的影响下,汉语不仅在诗歌中是“诗化的语言”,而且在其他各种文本中都称得上是“诗化的语言”。
保罗·利科从一词多义现象出发,指出科学语言是一种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是人工形式化的语言,具有一套消除歧义的矫正程序,它倾向于排斥活生生的经验交流。而诗歌语言正好相反,它推崇歧义,同时构建多种意义系统,具有一套保留和创造歧义的程序。诗歌通过增进符号的可感知性,加深符号和对象的根本分离。在诗歌中,词语的组合比词语的选择更为重要,隐喻使诗歌成为一种瞬间的言论创造物,而象征则使诗歌成为一个连续、持久的隐喻。利科还阐述了诗歌语言策略的意义:诗歌展示了一个我们能居住于其中的可能的世界,诗歌的真理表明了我们“在存在中存在的态度”而非可证实的陈述。因此,我们同时需要两种语言,以便在精确地描述世界的同时能对世界保持敏感。{5}
在中国文论中,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关于“蓄隐”的论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正是由于“文外之重旨”和“复意”的存在,文学文本才能“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从而成功的传达出审美经验。
伽达默尔也注意到了诗歌语言的自律性——诗歌语词见证它自身,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实,他认为诗歌和真理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用诗歌来谈说、揭示真理,就是要求诗歌语词拒斥“外在的证实”,从而帮助我们接近世界。{6}神学家奥特的看法与利科和伽达默尔的论述极为相似:
诗歌表达的东西比每种单一的、即或感触甚深的解释更多。每种解释,每种沉思都是个别人作为人的领会。与此相反,作为象征的诗本身表达的是与许多人、也许无限多的人相关的真实。{1}
这就是说,多义性或者说复义是诗歌的重要特性,它能把人引向真理。正如雅各布逊所说,“含混性(ambiguity)是一切自向性话语所内在固有的不可排除的特性,简而言之,它是诗歌自然的和本质的特点”{2}。复义的产生,与自我指涉有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自我指涉,所以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甚至根本无法确定,在阅读和解释之中就出现了复义或曰多义现象。但有人对二者的区分持怀疑态度,比如高友工、梅祖麟就否认诗性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③考虑到他们的专业背景,这种观点并不奇怪。
这些解说对于诗歌的形式特征的强调,大都与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有关。文学性和诗性,在形式主义者那里是一对近义词。为了与传统的文学观念对抗,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于诗歌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着力从语言形式上将诗歌(文学)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其语言观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而诺瓦利斯的纯艺术观念则与康德的“纯粹美”概念有关。
对于古代汉语文本来说,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之间的区分可能更为困难,因为很难找到以“标准语言”写成的文本。更富有意味的是,日常语言在汉语文本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反倒是诗性语言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因此,当我们使用“诗性语言”或“诗性”之类的概念来分析和评判汉语文本的时候,就很容易置身于一个错位的情境之中而不自知。
三、自我指涉
在形式主义的语言观中,还有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表述和界定的概念,就是“自我指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都不太关注言语(文本)所谈论的现实,而将目光投向其谈论方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指涉自我的语言(self-referential language),即一种谈论自身的语言”{4}。马里奥·瓦尔代斯也提到,“对话语的描述性分析说明,外部指涉对象在诗歌语言中被淘汰,诗歌语言实质上是自我指涉的”{5}。
所谓“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又译“自我参照”、“自我指称”、“自我相关”、“自我涉及”,简称“自指”。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指涉现象并不少见。比如,“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个类似于语言游戏的故事,以及“不许说话”(一个人为了保持特定时空的安静而不得不一再制止别人说话)、“禁止张贴”(张贴在墙壁上的标语)之类的语句。
在计算理论中,自我指涉与递归定理有关,一般译为“自引用”,指的是一个程序运行之后所输出的数据就是它自己,如同普通语言中的句子“打印这个语句”,它既是指令又是执行指令所得到的结果。{6}自我指涉与人工智能以及数理哲学中的集合论、递归论等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
在逻辑学中,自我指涉“是指一个总体的元素、分子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又指称这个总体本身,或者要通过这个总体来定义或说明,这里所说的总体可以是一个语句、集合或类”{7}。它与悖论的关系很密切,如说谎者悖论。许多学者将自我指涉视为导致悖论的原因,主张以禁止自我指涉的方式来消除悖论。也有人认为自指现象不可能消除,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怪圈。维特根斯坦等实证主义者将形而上学命题一律视为同义反复:“逻辑的命题是重言式。因此逻辑的命题就什么也没有说。”{1}因此,大多数传统的哲学命题(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对范畴和时空形式的证明等{2})都是自我指涉的命题,无法通过逻辑和经验来证实,因此是无意义的。
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著作中,自我指涉是一个关键词,其含义要稍微宽泛一些。卢曼借助“自我指涉”或“自体再生”来描述社会系统的封闭性:
系统依靠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生产出另外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自我指涉系统是作为一个要素生产的封闭网络而存在的。这一网络不断地生产一些要素,而后者又被用来继续生产另外一些要素。由此,该网络便把自身作为一个网络再生产出来。③
如果自我指涉是系统的基本特征,系统就只能通过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结构和过程来回应环境的变化,而不能直接与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卢曼还将自我指涉分为三种类型:自反性(reflexivity)、反省(reflection)、基本自我指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指涉结构已经居于统治地位。但美国学者拉什认为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概括现代主义的准则。{4}
自我指涉概念在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也有广泛的运用。在心理学领域,记忆的自我指涉(自我参照)效应广受关注,它指的是当一个人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时,印象最为深刻。{5}美国学者波齐认为,近代国家是一个功能高度分化的体系,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的高度制度化,即非个人化、形式化。但是,“不管是作为整体还是国家的某个机构,国家均容易陷入一种只考虑自己专门事务的倾向,每一个机构均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更宏观的社会现实,因而表现为自我指涉的特点”,“这样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机制的作用结果是推动了该机制大量生产自己的产品”。{6}比如公司生产部门生产过多的产品,立法机构制定过多的法律,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大学培养过多的博士,等等。
在文学领域,自我指涉除了用来描述诗歌的特征之外,也可以描述一部分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尤其是“新小说”或“元小说”。在雅各布逊等人看来,诗性在一切文本中都存在,诗歌只是诗最活跃并压倒其他功能的一种言语模式。托多洛夫则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反性的,“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都是通过它编造的事件来叙述自己的创造过程,自己的历史……作品的意义在于它讲述自身,在于它谈论自身的存在”{7}。关于自反性(self-reflexive),《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有一个解释:
该概念适用于描述那些公开揭示自身人工雕琢过程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小说中往往能够发现此类自我指涉的特性,这些作品一再提及自身的虚构性特征(见“元小说”条目)。在此类作品——以及早期的同类作品如斯泰恩的《商第传》(1959-1767)——中,叙述者有时被称作“自觉的叙述者”。自反性在诗歌中也屡有发现。{8}
正像自我指涉在哲学中带来了种种理论上的困惑一样,艺术中的自我指涉(元小说、先锋诗歌、行为艺术,等等)也带来了阅读、批评和理论上的困难。关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自指性,罗曼·雅各布逊的表述更为明确,他将语言的基本功能概括为六种,即指称、交际、诗性(poetic)、表情(emotive)、意动和元语言功能,认为“诗歌功能对指示功能的优先地位不是消灭指示作用,而是使指示作用变成了含混的作用……运用连续结构的对应原则造成反复是诗歌的显著特点”{1}。
诗性语言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使语言的结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音节、重音、长短音、词序、句法停顿等方面的对应关系,突出了符号、形式和结构,突出了语言的能指,甚至使得能指本身变成了所指。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宣称,诗歌的语言是一种诡论(paradox)语言,科学的语言必须清除诡论的痕迹,而“诗人要表达到真理只能用诡论语言”{2}。就这样,哲学家们所要尽力消除的悖论和自指现象,在文学批评家们看来却恰好是诗歌语言所必不可少的建构规则。自我指涉与诗性的内在关联,还可以在斯拉文斯基的概括中看出来:
语言的其他功能使话语归向外部世界;诗歌功能则是要建立一个有内部理据的话语“世界”。……诗歌功能要把陈述本身变成对象,要限制陈述作为感情、概念和指令载体的作用,要突出其作为一个新“物”的自我价值。③
在汉语当中,由于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文本、科学文本和法律文本,自我指涉的广泛存在并未带来心智上的困惑。而自指现象在文学文本(尤其是非叙事性的文本)中不仅不会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障碍,反而常常有助于文学性的增强,所以,汉语文本的自指结构至今未受关注。
四、诗性智慧
除了“诗歌”这个亲缘关系最近的概念之外,汉语学术界所使用的诗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维柯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在《新科学》中,维柯用了约一半的篇幅来讨论诗性智慧,将“诗性智慧”锻造成了一个关键词,他所提到的“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历史”、“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宇宙”、“诗性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等概念,涵盖了诸多我们通常以为本不具备诗性的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证明各民族的发展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
诗的真正的起源……要在诗性智慧的萌芽中去寻找。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4}
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的诗人。{5}
维柯认为诗性语言早于散文语言,最早的民族都是诗人。诗是人内在的情感、精神世界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于本无感觉的事物”{6},通过这样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人类将陌生的、异己的外部世界建构成了可以信任和栖居的家园。当然,人类不仅仅是通过诗歌建构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还逐渐建构了一个逻辑的世界。诗与哲学、历史等话语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得到过精辟的阐述,但维柯的论述还是令人豁然开朗:
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诗性语句是凭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的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1}
诗始终与情感、感觉、想象、形象相伴,而哲学则与推理和抽象思维相伴,这早已是西方思想中的常识。维柯并没有赋予“诗”或“诗性”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其贡献仅在于用此概念对人类文化作了一次宏观的描述,从而阐发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已经为我们所熟知,此处不再详述。
维柯借“诗性智慧”一说来为原始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制度辩护,指出“现代”文明的根源其实是原始文化,但他并不认为诗性智慧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智慧。反观中国文化和汉语文本,在文明程度长期领先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显著的诗性特征,这难免令人惊讶。尽管只有西方世界发展出了思辨理性和现代科学,但中国人对此常常难以释怀,西方文化仍然是汉语思想所难以消化的他者(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理智上),维柯之所以受到中国学术界关注,当与此类情结有关。
五、原始思维与互渗律
“诗性”一词与维柯的诗性智慧有关,而诗性智慧又主要是指野蛮民族或原始社会的智慧,则我们不能回避布留尔和斯特劳斯关于原始思维的论述。
布留尔从现代人所习惯的逻辑思维出发,将原始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认为它是受“互渗律”支配的:
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想说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这一情况使我们很难于探索这种思维的过程。{2}
逻辑思维和原始思维的分界线,就在于二者对于矛盾的态度。在布留尔看来,互渗律是原始思维的最重要的原则。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不是源自智力活动,它带有情感性,并且变动不居。原始人常常将肖像与原型混同,并且相信“可以通过对肖像的影响来影响原型”③,他们还会把任何偶然出现的事物当作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原始意识往往根本不考虑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而特别关注现象之间神秘的、不依赖经验的联系。原逻辑思维的神秘性在后来的逻辑思维中仍然留有痕迹,但抽象概念只有不停地扩展,才不至于凝结为僵化、自足的体系,不至于使智力活动蜕变为捕风捉影、空洞无物的议论。布留尔认为“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4}。
维柯指出了人与物的交融,布留尔则以互渗律来概括表象之间的交融。布留尔还认为,逻辑思维必然要“随概念的明确性和限定性一起增长,而这种明确性和限定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则是集体表象的神秘的前关联的减弱”{5}。逻辑思维在一些文化中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原因就在于这种受互渗律支配的表象联结方式,或者说诗性思维。
原始思维是否对世界充满好奇?布留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始民族常常显得过于老成、自负,急于对世界进行解释,而不太考虑它的“世界观”能否经得起事实、经验的检验。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随着社会活动领域的不断分化,原始思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也许只有在艺术活动中才保存着一席之地。
与布留尔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将巫术看作“犹犹豫豫摸索着的科学”,因为原始思维有着自身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原始思维(神话思维)所建立的诸种结构,为科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它“不只是被禁闭于事件和经验之中,不断地把这些事件和经验加以排列和重新排列,力图为它们找到一种意义”{1},而且将人从无意义、无秩序的偶然世界中解放出来。卡西尔也认为神话思维“决不缺少原因和结果的普遍性范畴”,而“整理混沌的感觉印象、即按照相似性选出确定的类别并形成特定的系列,这对于逻辑思维和神话思维来说是共同的”{2},但他同时指出,神话思维“全然不了解对于经验科学的思想似乎是绝对必然的某些区别”,比如事实和感觉、愿望和实现、影像和物体、整体和部分、空间和时间、属性和实体,等等,从而在因果概念和客体概念等方面与逻辑思维截然不同。
六、“诗性”概念的蜕化
这个谱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比如“文学性”和“审美”就是另外两个与之关系密切的概念,鉴于前者与“诗性语言”有理论上的亲缘关系,后者则意义显豁,此处不赘。有论者认为,“诗性”概念的流行与海德格尔著作的译介有关,多数学者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层面上谈论“诗性”,混淆了海德格尔与维柯的背景。③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似乎高估了这一概念的某些使用者。总体来说,“诗性”概念有一个复杂的谱系,难以从中选取一个概念来最终规范、界定“诗性”,也难以将其融合。{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概念越难界定,越是缺少约束力,便越容易流行——这种情形曾经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发生,“后现代”、“人文精神”、“文学性”、“现代性”,等等,都是概念蜕化的典型案例。
西方思想对于诗性、诗性语言、诗性智慧的关注,不单纯是文学或美学上的,而与西方思想中的形而上学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西方世界,文学与哲学、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源头和精神追求,有着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对于真理、实在、超验、彼岸以及自我、人性、心灵等问题的关切,往往促使西方思想家跨越艺术与科学、哲学之间的边界,把目光转向文学。正如怀特海所说:“哲学与诗同源。二者都寻求表现对终极的善的感受——我们称之为文明。无论是哲学还是诗,都要形成超越语词直接涵义的形式。诗与韵律为友,哲学与数学模式结盟。”{5}诗性智慧、互渗律等概念,其实也是哲学与诗相结合的产物。
许多学者喜欢引述洪堡特的观点,来证明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却忽视了洪堡特关于诗歌和散文之关系的论述:
如果语言具备真正发达的形式,诗歌和散文就会依据一定的规律同时成长起来……诗歌的倾向和散文的倾向必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助人深入扎根现实,但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愉快地超越现实,得到更自由地发展。倘若一个民族地诗歌在全面、自由和灵活地成长起来地同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相应发展创造下可能性,就不会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6}
诗歌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英语诗歌;语音象征;诗歌韵律
索绪尔(F.D.Saussure)(1980:101)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英语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富有音乐性的语言。诗歌之所以一直受人青睐就是因为其节奏鲜明、富有音乐感。正是这种鲜明的节奏,才把诗歌与小说、散文等文学种类区分开来。诗歌的节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命力,也是为人们广为传诵的原因之一。
一、诗歌的语音象征
语音象征主要体现在词汇的语音层面上,语篇中巧妙地运用语音象征能够产生一定的表意功能,取得特定的文体效果(项成东1993)。例如:
The sound must be an Echo to the sense:
Soft is the strain when Zephyr gently blows,
And the smooth stream in smoother numbers f lows;
But w hen loud surges lash the sounding shore,
The hoarse, rough verse should like the torrent roar.
(A. 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
诗中第二行通过/ s/ , / f/ , / r/ , / n/ , / l/ 等柔和型辅音的连续运用, 摹拟“微风轻佛, 平静柔和”的意境;第三行通过长元音/ u: / 和/ u/ 以及辅音/m/,摹拟“平溪静流”的音响;第四、第五行通过节奏变换,连续运用重读音节,产生了“惊涛拍岸”的紧张激烈的音响效果;另外双元音/ au/ (loud, sounding) 和长元音/o : / ( hoarse, roar) 的巧妙运用象征惊涛骇浪发生的回荡声响。
二、诗歌语音的谐音双关
语音的谐音双关,是指利用字、词间的发音相同或相似的关系,一语双关地表现两件事情或两种内容。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的外部言语中,最常用语音手段就是谐音双关的手段。诗人利用词语间的谐音一语双关地表达其微妙的主观情感。英语诗歌中,诗人也常使用语音的谐音双关手段建构诗歌意象语言的外部言语,委婉地传达诗人的思想情感。
如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茵纳斯弗利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中,“Innisfree”(茵尼斯弗利岛)是爱尔兰西部的一个湖中小岛,诗人将这一小岛选作诗歌的中心意象,通过对它的描写,诗人将美丽宁静的大自然同车道纵横的人类社会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词语“Innisfree”承担了诗歌主体意象词语,同时“Innisfree”一词在发音上类似“inner’s free”,诗人通过运用这种谐音,含蓄地表达对“inner freedom”(内心的自由)的向往。这首诗的风格与中国古典诗歌《饮酒・结庐在人境》(陶渊明)非常相象,都表达了想要远离嘈杂、忘情遗事、融入自然的心态和强烈愿望。
三、诗歌的韵律
诗歌语言的特点是它有优美悦耳的韵律。这种韵律体现在诗行之间和一个诗行内的押韵上。押韵使诗歌和谐、优美,读来琅琅上口,余音袅绕。同时,一个熟悉了的韵律反复出现,会使人感到听觉上的满足,并产生美的共鸣.同时,韵律又常常与人们表达的感情有关系,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基本的韵律,下文简单介绍几种。
押韵按押韵音在诗行中出现的位置可分为:尾韵(end rhyrne)和行内韵(internal rhyme)。尾韵(亦称脚韵)是指押韵在诗行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上。行内韵则是诗行中间的停顿或休止前的重读音节与该行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押韵。这种押韵法,在诗行停顿的节奏感上,又为诗歌增强了更强的音乐感。例如,英国诗人Thomas Nash在Spring《春天》一诗中写道: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
Then blooms each thing, then maids dance in a ring,
Cold doth not sting, the pretty birds do sing,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这一节用鲜明的尾韵和行内韵,使得全诗节奏明快,韵律强烈,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了春天的欢乐,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另外,该诗结尾处重复使用拟声词,模拟悦耳的布谷鸟叫声,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如身临其境,尽情享受大自然美妙的乐曲。
四、小结
在优秀的诗篇中,声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为诗歌的意思服务,是表达意思的一种手段。在声音的配合下,诗歌的外在美和内在美交相融合,在形式和内容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也是诗歌区分于其他文学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
【参考文献】
[1]陈波.论英语诗歌的美感[J].黑龙江:鸡西大学学报,2008(3).
[2]刘芳.诗歌意象语言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3]任裕海.能指与所指: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初探评[J].北京:外国文学研究,1997(2).